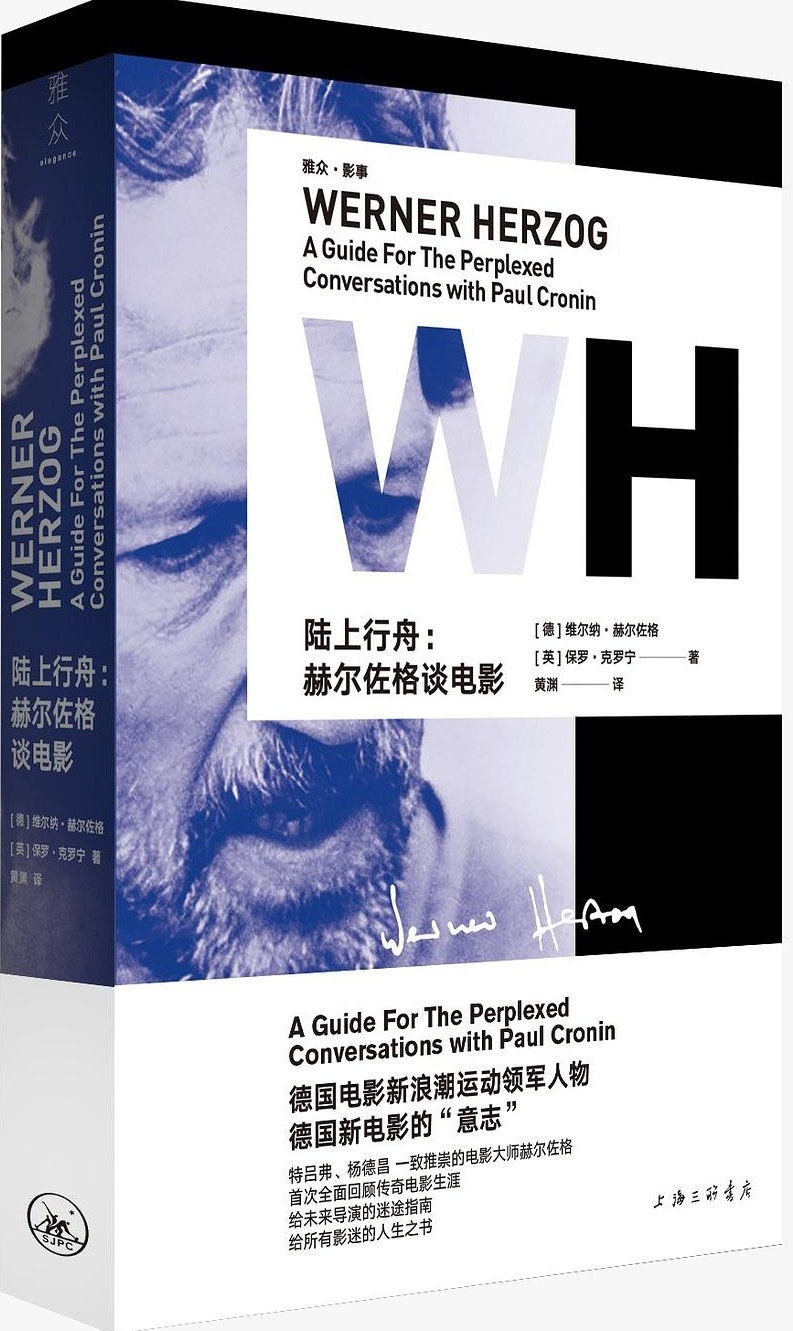
你为什么要拍摄《忘梦洞》?
这片子说的是法国南部的肖维岩洞,一九九四年,人们在那里发现了已知最早的洞穴艺术,距今有三万两千年的历史。在我的人生中,第一次不受家人、朋友影响,独立形成的知性觉醒,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某种文化产生强烈兴趣,那是在我十二岁那年,地点是在慕尼黑一家书店里。书店的橱窗里摆着这么一本书,封面是拉斯科岩洞里的史前绘画,画的是一匹马。那一刻,我心灵受到了强烈震动,整个人再也无法平静。那种兴奋劲,没法用文字来描述,而且至今都还记忆犹新。我告诉自己,必须把这书弄到手。此后,每周经过这家书店时,我都会心跳加速,担心它会不会已经被别人买走了。估计那时候我天真地以为,这书全世界就这么一本。我在网球俱乐部当了半年多的球童,终于存够了钱,把它买了回去。第一次翻开它时,那种敬畏的感情,让我整个人颤抖起来;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人就是这样,小时候迷恋上的东西,会一路跟随我们。那本书我一直都留着,后来才发现,其实里面那些东西写得相当肤浅。
距离影片开拍还有一段时间,我第一次获准进入了肖维岩洞。洞里的一切,感觉都像是才刚留下的。那种新鲜程度,令我大吃一惊。洞熊这种动物,早在两千年前便已灭绝,但肖维岩洞的地面上,留有明显的熊迹。某处壁凹的地方,留有小男孩的脚印,再往边上一点,还有一串狼的足印。是不是有一头饿狼在追赶这孩子?又或者他们是朋友,一起进了这岩洞?还是说这两处足印,根本就是相隔几千年,分别留下的?洞里有驯鹿的画像,但那人显然没有画完,之后又换了个人,才告完成。叫人吃惊的还在于,同位素测定表示,这前后两次绘制,中间竟相隔五千年。透过这深不可测的时间深渊,我们这些后来者还有没有可能理解那些史前艺术家究竟在想些什么?岩洞附近就是阿尔代什河流经的山峡,河上是六十米高的天然石桥—拱桥(Pont d’Arc)。岩洞周边的风景同样叫人叹为观止,看到的人,肯定都会想起瓦格纳和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作品来。于是,三万年前生活在这岩洞中的艺术家,似乎也被拉近到了我们眼前。这里的风景不仅仅属于浪漫时期的艺术家,石器时代的人或许也同样感受到了它的力量。于是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在肖维岩洞的周围,还有着那么多个旧石器时代的岩洞。我和一位参与这个研究项目的科学家聊了一下,在他看来,对于三万年前住在这里的那些人来说,拱桥不仅是一处实际的地标,很可能也是他们神话故事中充满遐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们画这些画,具体是出于什么目的?
不同的岩洞中,都有蹲伏在地的野牛形象。所以,有可能是四处旅行的艺术家,从一个岩洞画到下一个岩洞。但是,我们甚至都没法确定,对于画画的人来说,那些画究竟是不是代表着艺术?或许,他们只是用它来练习打猎也说不定。肖维岩洞的诸种秘密,可能永远都无法参透了。我们只能参照那些不久之前还过着石器时代式样的生活的人——例如澳大利亚的土著,或是卡拉哈里沙漠的布希曼人——对照他们的文化,来做些有理有据的猜测。利用同位素测定,我们可以知道,两万八千年前,有人拿了一个火把,贴着岩壁划擦,想要重新燃起火焰。但是,同样是在这洞穴里,我们看到一块祭坛式的岩石,还有它上头小心翼翼放置着的熊头骨;没人能解释清楚它的确切意义。所有线索都指向了某种宗教仪式,但也说不定,那熊头骨只不过是哪个孩子的玩具。而岩壁不同位置上的那些手掌印,很明显能看得出来,那人的小手指有畸形,继而我们可以假定,那都是同一个人的手印。


关于岩洞的情况,之所以能了解到现在这种程度,主要靠的是现代的考古设备。岩洞地面上的每一粒沙子,都经过了激光测量。但即便如此,关于岩洞壁画的问题,仍旧缺少完整、明确的答案。我们只能更多地依靠自己的智慧与遐想。我敬佩在肖维岩洞里工作的那些科学家;他们在宣布各种新发现时小心谨慎,从不把精力浪费在用那些心灵层面、“新纪元运动”来诠释这一切的事情上。同时,我还尤其欣赏像朱利安·摩尼(Julien Monney)这样的人。在影片中,他告诉我们,这些科学家正通过科学的方法,提出对于岩洞的全新认识;但他也不忘补充,他们的主要目的——或者说,至少是他自己的主要目的—是要构想出关于那些岩洞的故事,几千年前在这地方,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和我一样,他也是既看重实证科学,同时也非常尊重人的想象力。有幸跟他对话,从一开始就让我深深着迷。尤其是因为,他在干考古之前,还在马戏团里演出过,是个多面手。

肖维岩洞里的都不是什么简陋的涂鸦,绝不是那种小小孩刚学会拿笔之后胡乱画出来的东西。距今几万年前出现的,已是具有充分完成度的艺术作品。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和现代艺术,相对于它来说,其实并无质的飞跃。那些岩洞画就是艺术的真正起源,甚至可以说是现代人类灵魂的真正源头。而且,那些画还都表现出了一种奇妙的自信态度。想象一 下,在当时的欧洲,绝大多数地方都被冰川与冰块覆盖着,海平面相比现在要低九十多米,但是在法国的一个洞穴岩壁上,却以比喻、象征的手法,呈现出了当时的整个世界。最妙的还是其中某几幅画作,竟有着能穿越时空的文化回响之声,那些人类与生俱来的视觉习惯,也由肖维岩洞,一路延伸至了千万年后的今日。岩洞中出现的人类形象只有一处,画的是一头野牛正拥抱着一位裸女的下半身。我们理应自问,为什么毕加索那一组关于半牛半人的弥诺陶洛斯和女人的画作中,也用到了同样的主题——他画这些的时候,并不知道有肖维岩洞的存在。另一个跨越历史长河获得延续的视觉习惯,便是岩壁上画的那些奔牛。在北欧神话里,奥丁骑的那匹名为“斯雷普尼尔”的马,长有八条腿,所以跑起来风驰电掣。注意看肖维岩洞里的那些野牛,同样也是八条腿。

你在片中谈到了岩洞画里的“原电影”元素
有证据表明,岩洞的地面上,曾经有人生过火,但是这处岩洞,从来就没人在里面居住过。在洞里找到的四千块骨头中,并没有人类的。也就是说,之所以会有人在洞里生火,可能是为了照明,而非烹饪。在岩洞因为那次严重滑坡而彻底封闭了上万年之前,或许也曾有光线能直接照进洞内幽深之处。但是岩壁上的那些画,位置都离洞口有一些距离。这意味着,作画的人一定是顶先在地上生起了火,然后站在摇曳不定的火光中,创作他们自己的影子,也会成为那些画面的一部分。因为火光跃动的关系,而《摇摆乐时代》(Swing Time)里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和他自己影子一起跳舞的那场戏,而那也是我看过的所有电影里,最喜欢的段落之一。在他身后是一堵白墙,三个巨大的黑影投在墙上,它们淘气地自顾自跳起舞来,不再像是他的投影。弗雷德也只能追着它们跑,最终重新拿回自己的影子。你不妨想象一下,这段戏是怎么拍的;想明白了这一点,会更觉得它真是了不起。他们一定是先拍了弗雷德跳舞的画面,以此制成影子的画面,将其投射在墙壁上,然后再让他配合影子一起跳,动作和节拍都要配合得天衣无缝。换作现在,这样的戏肯定会用电脑来做了。

让一个巴伐利亚人在肖维岩洞里拍电影,法国人作何感想?
我当初确实也挺吃不准的,怎么才能获准做这件事。毕竟,一旦涉及文化遗产,法国人还是相当有地域概念的。只是在我看来,那岩洞确实属于法国人没错,但同时也属于全人类。我始终有种感觉,就应该由我,而非其他任何人,来拍摄这部电影。结果我很幸运,第一次和法国文化部长会面谈这件事时,他一上来就坚持要我先听他说。结果他花了十分钟跟我介绍,我的电影对他如何如何影响深远。原来,几十年前,当他还是个年轻记者的时候,甚至还替法国电视台采访过我;当然,我是完全不记得这事了。但是,光他批准还不够,我们还需获得岩洞所在地各级地方政府的许可,同时还需得到相关的法国科学委员会的批准。我相信,最终我能获得所有这些人的认可,可能还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胸中熊熊燃烧的那一团火。
许可证一到手,我就向他们提出要求,能否在正式开拍前就让我先进去看看。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我需要在现场解决。结果,距离开拍还剩两个月时,我获准走进肖维岩洞,在那里待了一个小时。我想到了童话故事里赤贫的小女孩,繁星满天的凄冷夜晚,她独自徘徊在街头,忽然,天上下起一阵金币雨,小女孩赶紧扯起围裙;获准拍摄《忘梦洞》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是那个小女孩。在肖维岩洞的历史上,我很可能是第一个获准进入的非科学家。我是作为诗人进去的,我希望能调动起观众的想象。倘若这部影片从头至尾只有各种科学事实,我相信观众看过之后马上就会把它遗忘。而我的想法从一开始就很明确,我自己要靠边站,让艺术本身来说话。在我拍过的所有电影里,或许就数这部《忘梦洞》,最接近大家口中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那种纪录片。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尽可能清晰地将三万两千年前那些人留下的作品,给记录下来。
你这片子是用3D拍摄的
当初看到岩洞的照片,我感觉洞壁是平的,顶多就是稍稍有些小起伏。幸好正式拍摄前我能获准入洞,这才发现,洞壁上其实有着许多剧烈的凹陷,而那些古代艺术家作画时,巧妙地因地制宜,将那些凹凸融在了画作之中,相当具有表现力—举个例子,洞壁上一块凸起的岩石,被画成了野牛的脖子。所以我立即就想明白了,这片子必须拍成3D才行。而且我很清楚,在我们之前没有,之后也不会再有别的摄制组能获准进去拍电影的了。于是,这更坚定了我拍3D的决心。本身我对3D电影谈不上有什么兴趣,在此之前从没拍过3D,今后也不打算再用。但是在这岩洞中,就必须要用3D来拍,这已经不光是出于合理性的考虑了,更是我势在必行、责无旁贷的选择。“这次进行3D拍摄,一定不能表现得太刻意,”我对彼得·蔡特林格说,“不能让观众觉得,我们是有意要他们注意3D的特殊拍摄范围。”因为3D画面的关系,那些画作效果凸显,呼之欲出。影片结束时,观众之间所谈论的,不会是自己才刚看了一部电影。相反,他们说的都是,跟着镜头,刚才他们是真的进了那个岩洞。

要知道,当初肖维岩洞刚被发现时,法国政府第一时间便认识到了这颗时间胶囊的重要意义,于是尽其所能,对它做了全面保护。目前阶段,除少数科学家之外,它不对任何人开放;而且即便是那些获准进入的科学家,具体操作时也格外小心谨慎。法国政府采取的所有这些保护措施,绝非一时心血来潮。多尔多涅省的拉斯科岩洞和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岩洞,都因为游客呼气制造出的霉菌,蒙受了不可逆转的破坏。批给我们的拍摄时间,一共只有六天,每天只允许进去拍四小时,一次只能进去三个人。所以对我们来说,那真是分秒必争。只要进到里面,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得坚持拍。带进去的设备也有规定,只能靠自己硬拿,不可借助别的工具。那也就是说,分量重的机器,全都没法使用。还有灯具,也只能带不会散发热量的照明设备进去。洞里铺了一条六十厘米宽的金属步道,我们必须始终都站在那上面,脚不能沾地。所以拍摄某些画面时,我得抓紧了彼得的皮带,好让他尽可能地前倾身子,再将摄影机整个探出去,拍摄那些黑暗的角落。岩洞里一直都有毒气积聚——既有二氧化碳也有氡气——而且浓度不低。所以我们每次进去,都会有一位工作人员陪同进入,随时测量空气成分。这些都还不算,我们还得想法子应付3D摄影机,它不光是体积大,而且操作起来很碍事,上面满是各种对精度要求极高的机械装置,拍摄不同的镜头时——例如特写画面——还需专门重新装配一遍。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就着昏暗的光线,在这狭窄的金属步道上,完全靠自己——外面的人没法给我们任何技术支持,因为每次我们一进洞,身后的大门就关上了,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洞内的空气状态不变——把它重新拼装好。在那里面,甚至连打喷嚏都是被禁止的。有一次,才刚进洞,我们的数字式记录器就停止了工作。于是我们只能从别的地方拆东墙补西墙,花了十五分钟,当场给它做了块电池。
进过洞的科学家里,有人告诉我说,在洞里听到心跳声时,实在是不敢确定,那是否来自他们本人。另一些时候,感觉就像是有一双双眼睛正看着自己,就像是在那些最黑暗的幽深之处,正有人在观察着他们。有人问过我,进入肖维岩洞,是不是感觉像是一次宗教体验。答案是否。干正事都还来不及呢。但有过那么一次,其他人已经都出去了,我独自在那黑暗中站了几秒钟。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谈谈那些鳄鱼吧
影片结尾处的补白里,我解释了自己是偶然发现那些变种白化鳄鱼的。我用旁白的方式告诉大家,它们生活在距离肖维岩洞几公里之外的一些大型温室中。那是一片巨大的模仿热带环境的生物圈,热量取自于附近一家核电厂的冷却水,那是全法国规模最大的核电厂之一。我并没有明说,它们之所以发生了变异,是因为核辐射的关系;但我相信,观众自己能得出结论。我想要大胆揣测一下,假使这些动物能逃出温室,进到肖维岩洞里头,看到周围的一切,看到墙上的绘画,它们又会作何感想。鳄鱼和影片剩余部分其实毫无关系,但这段尾声放在这里,也并非毫无来由的凭空创造。我想要表达的还是一个关于认知的问题,我们的子子孙孙,未来会如何看待我们现在所具有的文明。因为,对比在岩洞里创作了那些绘画的人,我们显然已经有了不同的文化背景。让我好奇的是,时隔三万多年之后,我们现在会如何认知这些绘画;然后,再往后一百代人,他们到时候又会怎么看。说不定,到时候我们就成了他们眼中的白化鳄鱼。那些动物出现在影片之中,我觉得真是恰到好处,但如果我要向一家好莱坞公司建议,在一部关于旧石器时代岩洞壁画的电影里,加入一些白化鳄鱼的画面,他们肯定会让保安把我轰走的。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要拍些鳄鱼,但事后证明,我还是弄错了。几个月后才有人告诉我,那些根本就不是鳄鱼。它们其实是短吻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