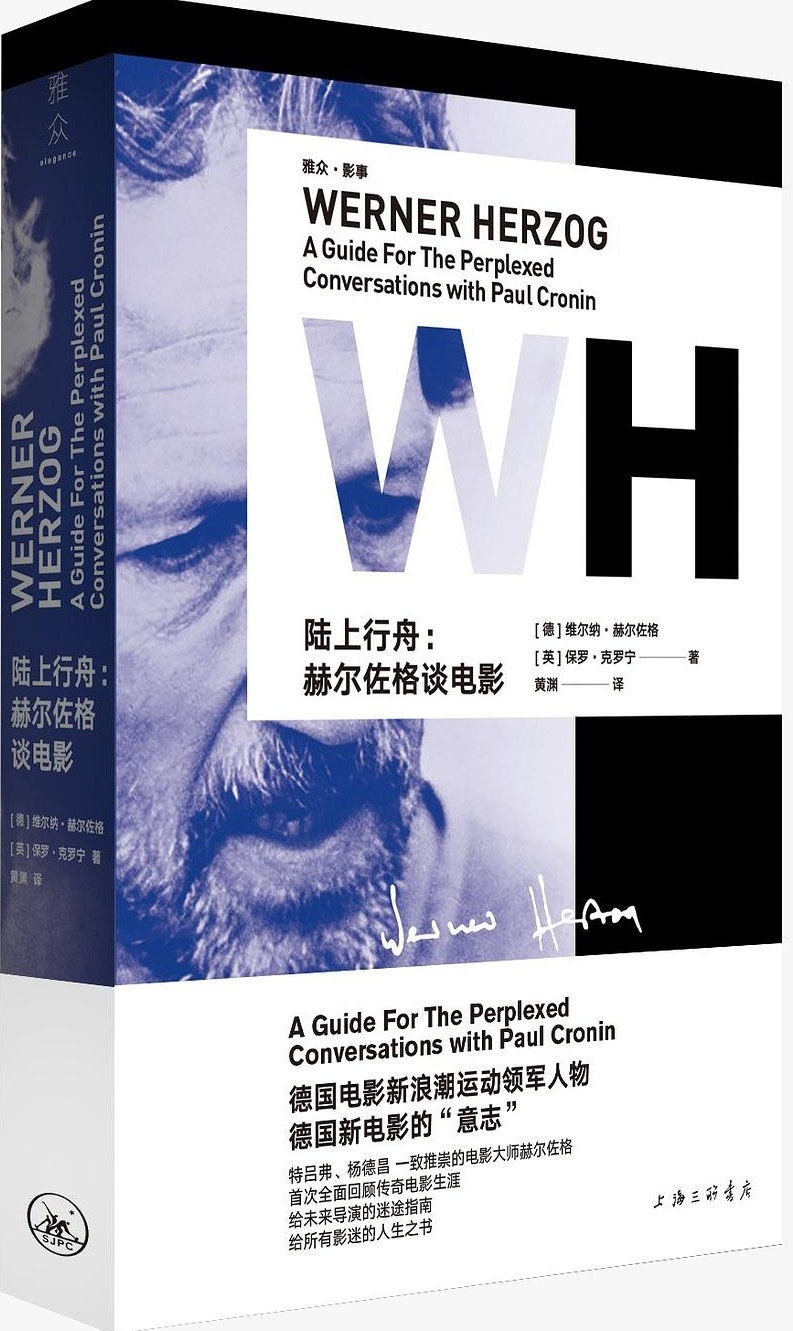
《白钻石》里的格雷厄姆·多林顿在主亚那丛林中,试飞了那假尚处于设计原型阶段的飞艇。
推荐我这个项目的,是我儿子鲁道夫,他觉得我应该做这个,因为它有着关于在空中飞行、翱翔的主题,故事情节上也和我本人对飞行的情感息息相关。它说的是航空工程师格雷厄姆·多林顿的事迹,他曾踩着自己的飞艇,由南安普顿一路飞到了将近一百六十公里开外的怀特岛。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他即将展开圭亚那之旅,挑战位于该国腹地的凯厄图尔瀑布——它落差极大,高度是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四倍——希望能成功驾着他那艘充满了氦气的飞艇,飞跃瀑布上方的丛林地带。他此行的目的,正是为了研究那些生活在茂密林冠中的野生动物。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那部分生物圈长久以来几乎都没怎么被了解过;人类对于海底深处的生物多样性,认识得都要比那地方更全面。如果是坐直升飞机上去的话,势必会造成巨大的噪音和旋风,飞艇就不一样了,风吹到哪里,它就飘到哪里。想要实现这类探险,最好的方案就是这种可操控的飞艇,而那也恰恰就是我朝思暮想的那种低调、内敛的飞行方式。
但这种飞法,势必伴随着很大的风险。一九九三年时一次类似的航行过程中,德国摄影师迪特·普拉格(Dieter Plage)驾驶单人飞艇,在苏门答腊岛上机毁人亡,便是前车之鉴。那艘飞艇的设计者和制造者,也正是多林顿,而且那也是它的处女飞,结果就不幸酿成惨祸。那次,它由六十米高空坠落地面,正砸在多林顿跟前。在《白钻石》的旧档素材中,普拉格的身影稍纵即逝,但不知怎么的,感觉却像是给整部影片蒙上了一层阴影。多林顿的故事让我想起希腊悲剧中那个做梦都想要飞起来的人。直至今日,都不能说多林顿已完全获得了救赎,毕竟,朋友的死会一直牵绊着他,直至他自己的生命尽头。拍摄过程中,连续有好几周,一谈到普拉格的事,多林顿始终选择回避。但我不断给他施压,某天终于把他逼得再也无路可退。“是时候了,”我对他说,“现在不讲,以后也再也不会讲了。”他半推半就地答应了,他也很清楚,那将会成为影片中的关键所在。我告诉他,现场只留三个人:摄影、负责录音的我,还有我十四岁的儿子。我当时有种感觉,能否让他敞开心扉,关键就是要让他面对一个少年,而非面对镜头或是一群剧组里的成年人,来谈这件事。
瀑布后头有个巨大的洞穴。
里面有一百五十万只筑巢的雨燕。它们会先垂直向下飞,时速超过一百六十公里,比小型飞机还快。然后再从这道水幕的边上——有些甚至直接穿透瀑布——飞出来。当我站在悬些的边上,它们就从我眼前扫过,快的跟子弹一样,但却完全没有撞到过我;即便飞行速度如此之快,它们还是能做到避开一切障碍物。我同了一位都落头领,那暗无天日的洞穴里头,究竟有些睡眠。他回答说,古人相信,那里面藏着财宝,还有负责看守的各种巨怪和体型庞大的毒蛇。我们让一位剧组成员——他是攀岩专家——背着摄影机,身上系好绳子,下到洞穴口,拍摄一下那瀑布后头究竟有些什么。结果,还是那位部落头领,恳求我千万别让那些画面被人看见,谁都不行。于是,我最终并未将它放在影片之中。
《白钻石》让我喜欢的地方在于,影片放到一半,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其核心内容起了变化,先是由多林顿转到了马克·安东尼·雅普——一位当地的拉斯塔法里教徒——的身上,继而又再转到了雅普十分心爱的那只非常厉害的公鸡“红人”的身上。类似这样的焦点转移,并非出自我原本的计划,而是当我在拍摄过程中,注意到周围这些剧中人物的具体情况后,故事线索与关注焦点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这样的偏移。影片将近结束时,我们的焦点已全放在了“红人”身上,它成了《白钻石》的新主角。克莱斯特在小说《米夏埃尔·科尔哈斯》(Michael Kohlhaas)里,曾有过类似的写法。故事讲了一半,焦点由主人公科尔哈斯转向了马丁·路德,最终又落在了一位吉普赛妇人身上。
时隔多年之后,你会不会又想起当初打过交道的那些拍摄对象?
当然啦。那就像是作为一家之主,你绝不会说那是一种职业,对我来说拍电影也是一样,那并不是一种职业;那就是我的人生。我拍过的那些电影,还有电影里的那些人,他们并非只是剧中角色,而是我身上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都是我内心的家庭一员;哪怕说,他们对我而言的意义,可能已今非昔比了,与当初拍摄那些电影时不尽相同了。
《沉默与黑暗的世界》拍完几年之后,菲妮就去世了,至于斯泰纳,我也有好几十年没和他联系过了。最后一次接触,当时他还在科罗拉多,替美国高台滑雪队当教练。布鲁诺·S是二O一O年去世的,至于他的全名全姓广为外界所知,那又是数年后的事情了。所以,不妨让我借此机会郑重地报上他的尊姓大名,以表纪念:布鲁诺·施莱因斯坦(Bruno Schleinstein)。他真是很善于发明创造,而且很为自己能完全靠着自学就成了钢琴家感到自豪。我们一起看《卡斯帕·豪泽之谜》时,他会捏我的手指尖。听到音乐声响起,他会说:“这勾起了布鲁诺心里强烈的感觉。”最终,我在《史楚锡流浪记》里特意为他写了些弹钢琴的戏。他平时还会画画,但要我来说的话,那只能算是“个性天真的”艺术作品。某天,他给我看了个大发现,说那绝对有必要送去德国科学院。他家里塞满了各种他由全市各处垃圾桶里翻拣出来的东西。他会搜集残旧的风扇,有些还能转,他就把上头的叶片分别刷上黄色、蓝色和红色。他发现,当风扇高速转动后,叶片上的颜色会忽然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一团白色。布鲁诺坚信,发现这一点的,他是史上第一人。晚年他还出版了一本警语录,办了自己的艺术展,发行了唱片。在许多人看来,我会用像他这么个人来拍戏,实在是太反常。几年前有人拍了一部讲他的电影,片子拍得很弱,而且抛出一个观点,说我利用了这个不谙世事、毫无城府的人。拍摄时虐待他,拍完后抛弃他。那片子的导演,就是个不值一提的傻瓜,对此我没有什么好作回应的。我只想说一句:本人问心无愧。而且让那种人作我的对手,他压根就不配;我宁可对手更强一些,难对付一些。那些年里,我和布鲁诺见面机会不多,但我一直都远远地留心着他的情况,如果真发现他遇到了什么麻烦,我肯定会第一时间出手相助的。
拍电影就是一种短期的投入,所以注定难有太多深层次的人际接触。如果我能按部就班地每隔五年拍部新片,那肯定会更易于维护这种人际关系。但事实上,我拍电影从来就不是这种节奏。我自己的生活状态本就相当漂泊不定,一年里走遍十几个国家,那是常事。我就像是中世纪晚期的佣兵,仗打完了,便转身奔赴下一片战场。几十年里我拍摄过那么多对象,没法一一保持联络,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好愧疚的。不管当初有多火热,合作拍电影时一起度过的那段时光,注定只能是稍纵即逝的一次牵手。类似这样的人际关系,时候到了,总会无疾而终。一旦合作关系结束,双方便很少再会继续有不断的接触。大家都有新工作要忙,相隔千里是常有的事。不过我觉得自己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交情最久、最深的那些朋友,恰恰是我入行之初,拍摄那些早期作品时遇上的。曾有一度,那也是我与人接触的唯一途径。幸运的是,这几十年来,每次拍新片,我总能召集到同一批合作伙伴中的绝大多数人,我一直信任他们。这里面也包括了我妻子,她是位照片摄影师,四处游历的幅度与强度并不亚于我。有时候,她会在我剧组负责拍剧照,于是我们就能携手同行于世界各地了。
长期以来,在我的合作伙伴中,有许多人并不一定非得是电影圈中人,但他们全都以各种极其相异的方式,为这些影片的制作贡献良多。这群个性顽强的男男女女,全都有着特立独行、天马行空、专注投入的特点,值得我去信赖。他们都心怀伟大的信念,全都和我一样,有着一颗驿动的心。乌尔里希·博格菲尔德是我好几部电影里的布景设计,同时,他也是一位研究普罗旺斯古代语言和游吟诗人文学的专家学者。还有几年前去世的克劳德·基亚里尼(Claude Chiarini),他是位医生,在巴黎精神病院担任神经学专家,过去还加入过法国外籍军团,原先又做过牙医。拍《玻璃精灵》时我们请了他来,以防备万一有哪位演员被催眠后,怎么都醒不过来的情况。此外,他也为我们拍了不少剧照。然后还有科尼利厄斯·齐格,他既是数学家,又是大师级的木匠,心灵手巧,就没他造不出来的东西。如果是在丛林深处拍摄,遇到电池故障的情况,他搞些树皮、树脂,就能妙手回春。赫布·戈尔德是我好几部电影里的副导演,他是波士顿大学的古典文学教授,又会武术。我始终觉得,拍摄电影时有一点很重要,要让每位工作人员都意识到,自己并非仅仅只是一名雇员。他们更应是团队中极其宝贵的构成元素。凡事竭尽所能,尽可能把电影拍到最好,这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利益相关的事。拍《陆上行舟》的时候,负责洗印胶片的一位技术人员,事先就仔细读了剧本,看片子的时候也拿出了电影导演的劲头,甚至还会专门留言问我:“特写镜头都在哪里?”
你曾经留小胡子留了好多年。还有你身上的刺青,现在还有吗?
那胡子长得可真不错,它就像是某种防御屏障,我可以躲在它后面。但经历了生活中的各种磨难,后来我把它剃了。事实上,那是因为我跟人打赌输了。反正,生活也待我不薄,可能我就是不再需要这屏障了。至于那个文身,你不提的话,现在我一般都不会想到它。它仍在那儿,在我手臂上。那是死神的图案,他身穿燕尾服,系着领结,对着一支老式的德国电视二台的麦克风歌唱。我已经好多年没去特意注意过它了。当初我才三十六岁,那是在旧金山文的,陪我朋友保罗·格蒂(Paul Getty)一起去的。保罗打算文身,我在边上看着。很快,文身师就让我看着迷了。既然是要等,索性自己也文了一个。
你曾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做过名为“二十世纪是否是个错误?”的讲座。
我曾和波兰作家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合作过一个有关科幻小说的项目。他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刚果东部那场骚乱为数不多的亲历者与幸存者。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光是被捕就有四十多次,还曾四度被判死刑。我问他,那段时间里最糟糕的经历是什么。他用自己一贯的轻柔嗓音回答说,是他住的小牢房里,忽然被扔进来几十条毒蛇的时候。“五天的功夫,我的头发全变白了。”他这人个性特别坚强,处变不惊,而且看事情一针见血。我们那次合作的想法其实也很简单:人类依赖科技,最终也会成为科技的第一位受害者。在我俩看来,科幻小说写的并不是未来的科学技术还能带给我们多大的可能性,而是因为科技的存在,我们未来将会失去的诸种可能。终有一天,我们会失去对科技的掌握,而且再也无法将它重新抓回手里。
类似这样的事,我们俩实在是见得太多了。机场里的电脑,键盘里长出了热带丛林的杂草,你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哪儿都飞不成了。我们也常面对彻底失能的电梯,走楼梯成了唯一的途径。我们还遇到过这样的事,城市的供水被士兵切断,一周之后他们又开着巨型的送水车,面对口渴的老百姓,待价而沽。我们还住过这样的旅店,行李员带着你进了房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灯泡来。只要你不在房间里,哪怕只是出去一小时,他们都会把灯泡拧下来取走。自行车坏了的话,修起来很容易,利用最基本的工具即可。汽车的话,少了汽油就是废铁一堆。如果哪天全世界范围内断电两星期,由此造成的混乱和痛苦,绝对难以想象。是否掌握一些最基本的技能——不靠火柴就能生起火来,懂得如何建造最基本的掩体,知道哪些浆果能吃哪些有毒——届时会成为生死攸关的关键所在。而这些,便是我俩心目中的科幻小说。
人类的狂妄自大总是让我深深着迷。人类总是试图在自然的环境中大兴土木,这种野心已经到了精神错乱的地步。看看那些建筑的样式,那些大而无当的东西,便都是最好的证明。它们已经危险地触及了禁忌。在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脉中的多罗麦特山上,耸立着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瓦伊昂大坝,其高度差不多有一百五十多米,当初落成的时候,是全欧洲最大的水坝。由它构成的湖区,四面八方都是陡坡,所以想当初就有少数一些持不同观点的地质学家,预言那会造成一场大灾难。一九六三年,那里发生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滑坡。灾变的那一刻,一块体积将近两千八百万立方的岩石,以惊人的速度冲入湖中,制造出的浪高几乎达到二百四十多米。这种类似于海啸的冲击,令周围数个村庄惨遭蹂躏,近两千人丧生。大坝本身倒是安然无恙,它底部的墙体厚达二十七米,用的都是最优质的钢材和混凝土,估计再过五十万年也还是岿然不动。人类自己造的孽,结果反而寿命比人类自己都要长久,瓦伊昂大坝便属此类愚蠢行径之一。
至于那些环保主义者,他们的基本分析并没问题,可一旦那些喜欢抱树的环保狂也参与进来,整件事就朝着负面发展了。他们盲目地只知道关注树蛙、熊猫和色拉菜叶的福祉,却不知道就在我们坐而论道的这会儿,很可能就有一门人类的语言渐渐消亡了。对于人类文化来说,这是不可逆转的损失,而且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发生着,绝对不容忽视。语言的消亡让人不胜唏嘘。想象一下当最后一个说意大利语的人消失之时,但丁和维吉尔也都随他而逝了。或是如果俄语再也不存在了,我们也就彻底失去了托尔斯泰与帕斯捷尔纳克。人类现在所说的语言中,百年之内,可能会有90%会逐渐消亡。在道德层面和文化层面上,这都是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不幸的是,人类至今都尚未能将其纳入共同的考量之中。在澳大利亚,两百年之前,还存在着六百种不同的语言,如今剩下的还不到其十分之一。拍《绿蚂蚁做梦的地方》时,我遇到一位上了年纪的澳洲土著,他住在南部奥古斯塔港的养老院里。他那门语言,会说的已经只剩下他这最后一人了。周围人管他叫“哑巴”,可他之所以不开口说话,其实只有一个原因:能与他语言交流的人,在这世上已不复存在了。我看着他在走廊里来回踱步,遗世而独立。他把零钱投入一台报废的饮料贩卖机,再将耳朵凑上去,就为听一下硬币落袋时的噼啪响声。这件事,他可以反反复复做上一下午。到了晚上,等他睡着之后,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会把硬币从机器里取出来,放回到他口袋之中。随着他的死去,人类共有的知识中,也有那么一部分就此失传了。
事实上,我们可以将彼特拉克(Petrarch)登山的那一刻,看作是事情最初开始出错的那一刻。那时候,他成了历史上为登山而登山的第一人,犯下了一宗“罪行”。在他用拉丁文写的信里,彼特拉克谈到他内心体验到的某种战栗;那可能是一种不祥的预感,预感到随之兴起的大众旅游,无需多久就会把山峦的庄严肃穆悉数剥离。在他之前,在我们没法具体界定确切时间的史前时代,人类也曾犯下过一桩重罪:饲养人类历史上第一头猪。回到旧石器时代,只有依靠狩猎和采集来生活的原始人。随后开始有人养狗,有助于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于漂泊不定的猎人来说,狗可以作为旅伴。养马也是同样道理,它是运输的工具。但是,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人类饲养的第一头猪,那却是不折不扣的原罪一桩。正是农业的出现,带来了定居的生活方式,并且最终导致了城市的出现,令人类变得久 坐不动。我们所有的问题,追根溯源,全都在这上头。如今再想让时光倒流,为时已晚。
请勿抱有幻想。尝试制服这个星球的同时,也请自担风险。人类是不可持续的。三叶虫和菊石也都在存在数亿年之后,从这星球上消失了。再往后,恐龙也难逃灭绝的命运。宇宙并未对人类网开一面,我们最终也都会彻底消失;但我从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相比我们,螃蟹、海胆和海绵的生存几率更高;它们都已在地球上存在了几百万年,未来或许还有几百万年的生命。作为陆地生物,我们要比蟑螂更脆弱。一直以来,大自然都对人类的存在拥有控制权。我们最终会毁灭在微生物手里。曾有人问马丁·路德,如果今天就是世界末日,他会怎么做。路德给出的答案,泰然自若地叫人惊叹。“我会种一棵苹果树。”他说。而我呢,我会拍一部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