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你不看完电影吗?”
——《热带疾病》中Tong在卫生间里被同伴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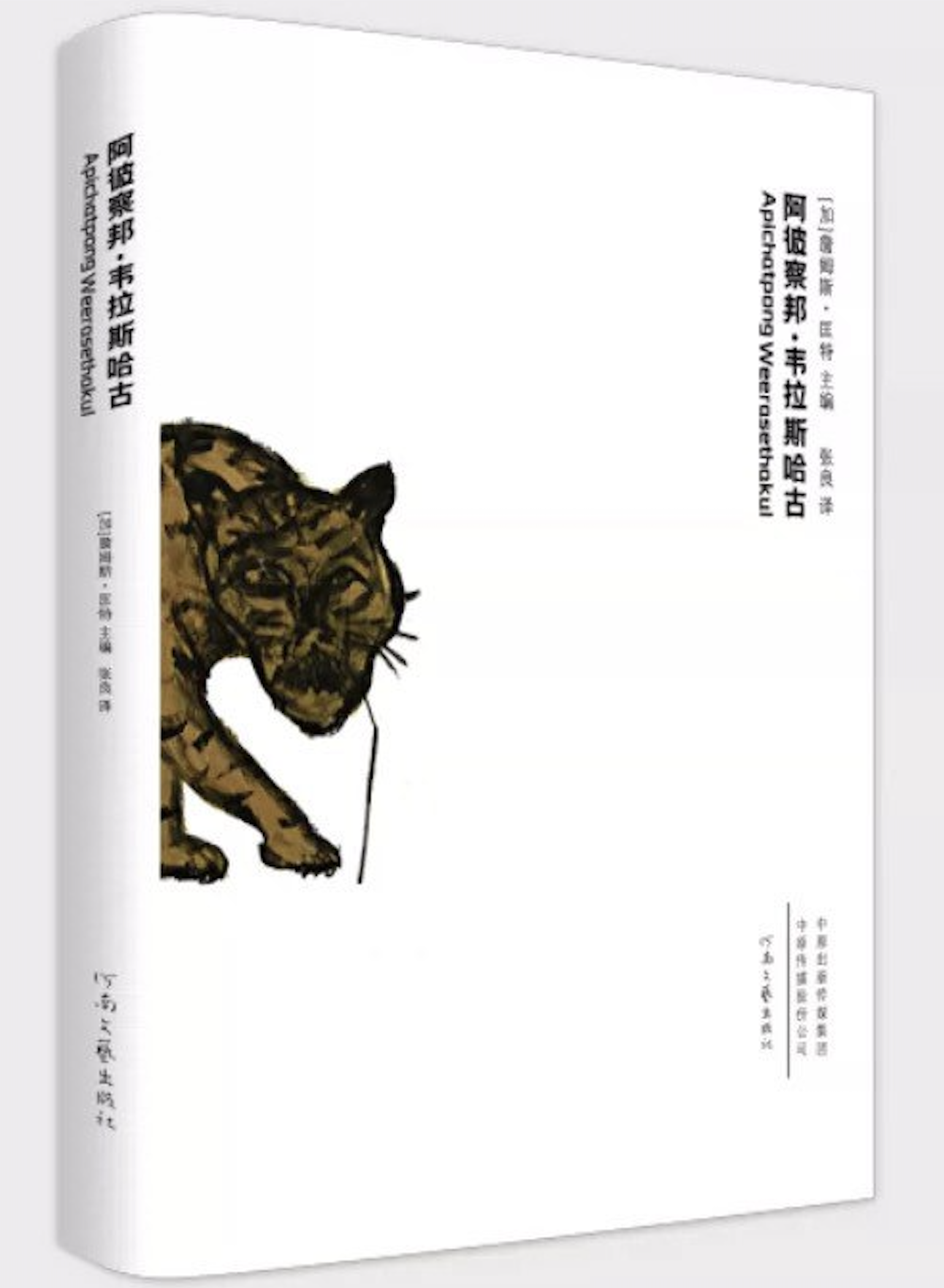
《热带疾病》开场段落中的尸体可能并不“精致”,它早已僵硬、裤子被拉下、屁股露出来,也许被枪杀之前还被强奸了,但它体现了阿彼察邦对在《正午显影》中所使用的雏菊环式1的超现实主义叙事方式的喜好。正如《祝福》中Orn通过提到一个名叫Keng的士兵指向了阿彼察邦的下一部电影一样,作为Orn情人的Tommy代表了《祝福》与《热带疾病》的又一个联系:在《祝福》中,他在画外被枪杀,然后在《热带疾病》的开场段落再次出现——一具穿着“同样内裤”(阿彼察邦也如是说)的尸体。同样是根据导演自己的说法,《祝福》中Orn看着自己浸在水中的双手的特写在《热带疾病》的下半部分也有一个有意识的重复,即护林队员检查自己受伤的手的特写。类似的,阿彼察邦曾经开玩笑地提到在《热带疾病》表现寺庙中的老妇人的场景中,《祝福》中的那把蓝色雨伞被“回收再利用”了。
这种再利用或者说重复其实也发生在这部电影的内部,即在上下两部分之间或者在某一部分之内。比如《热带疾病》的一开始,一名士兵拿着对讲机追求远方的女士,这可以与这部电影的下半部分出现的对讲机联系起来,它被破坏和丢弃在丛林里,通过它,虎灵被追踪并反过来追踪护林队员。在《热带疾病》的上半部分,一个头发浓密、带着幸福微笑的可爱男人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作为Tong的前男友出现在电影院的洗手间里,第二次是穿着紧身运动衫的健美操教练,第三次则是作为一个士兵。这部电影还有一系列的瞥向银幕之外的目光,比如最开始在字幕出现时Keng的试探性的、挑逗式的微笑,它们与其说显示了叙事的断裂,不如说更多的是对观众参与叙事空间的一种引诱以及对阿彼察邦的重复手法的一种提示。
也许是因为《祝福》收获了国际上的赞誉(在戛纳国际电影节获得了“一种关注”大奖),使得《热带疾病》获得了来自欧洲的电影制作资金,所以阿彼察邦可以更加直截了当地,甚至可以说是夸张地表现他之前的电影中只是略微提出或者暗示的东西,特别是同性恋的欲望(主题上)和二元分化(结构上)。为了求得更强的混合效果,《热带疾病》强化了《祝福》的二元结构,整部电影被分为两部分,它们各自独立、有自己的开场字幕,但又在叙事上相互关联。(相比《祝福》,《热带疾病》在戛纳的首次放映引起了更大的骚动,在第一个故事之后的黑屏持续了大约10秒,然后第二个故事的字幕才慢慢出现,这一度被当成了技术故障。)《热带疾病》被阿彼察邦称作《祝福》的“邪恶的双胞胎”,它将阿彼察邦早期作品的奇异性扩展到了萨满教的神秘领域。《热带疾病》先是讲了一个关于Keng 和 Tong的爱情故事,Keng是泰国中部一个森林巡逻小队的休假士兵,他在追求Tong,而Tong是一个在制冰厂工作的腼腆的乡村青年;然后又讲了另一个故事,一个士兵进入密林去追踪一头捕食了很多当地人家畜的野兽。这两部分像是一种对比研究:第一部分没有名字,有很多阳光、社交活动、对话,而且发生在城市中;第二部分则被命名为“灵魂之路”,被设置在茂密的丛林深处的黑暗中,在一个遥远、无言的夜晚的孤独状态下,到处都是嗜血的水蛭以及发着荧光的牛的鬼魂、天使般的萤火虫、可以心灵感应的狒狒、用电子沙沙声说话的树木,还有一只似乎代表了士兵宿命的老虎:它既是他的情人,又是他的毁灭者。在白日梦和精神错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对比之下,《热带疾病》像是把一个追捕者渴望与他的猎物、同时也是他的欲望对象融合的故事讲了两遍。但阿彼察邦所创造的神秘感在上半部分是寓于日常的,在下半部分则体现为万物有灵,这使得二分法某种程度上变得简单化了。更令人费解的是第一个故事中出现的那一段似乎有点漫长的令人不安的时刻,即为什么那个头发梳得油光的男人(也许是Tong的老友或者情人?)在卫生间门口转头对着 Tong露出电影明星般的微笑?以及在第二个故事那巨大的丛林中,当士兵用灼热的目光盯着老虎时,为什么士兵会屈从于那种黑暗的“疯狂之爱”(amour fou),或者说屈从于一种病态的欲望?

电影一开始引用的文字进一步体现出上下两部分截然不同的情绪和风格:上半部分引用的是日本作家中岛敦(AtsushiNakajima,1909-1942)的话(包括电影本身以及大部分资料都错误地引为泰国作家Ton Nakajima),第二部分引用的是泰国作家诺伊·因塔农(Noi Inthanon,1906-1963)的话,这本身就给了这部电影一个人类文明与自然世界相对照的架构。
根据日本大百科全书记载,中岛敦很年轻就死于肺炎,他以“文字优美、博学、悲观”著称,继承了他父亲对其他亚洲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学术兴趣。诺伊·因塔农是作家马莱·乔菲尼特(Malai Choophinit)的三十多个笔名之一,他被誉为泰国的海明威,被认为是泰国最优秀的文体家之一,他以本土主义小说和猎人与他的村民助手一起冒险进入野外的探险故事而闻名。阿彼察邦非常欣赏诺伊那种唤起人们对夜间丛林的恐惧的语言,这无疑成为他自己涉足这个夜间世界的一个样板。(这位作家的后期作品对乡村的社会和政治冲突所做的更多探索,可能也为阿彼察邦的最新作品《原始》提供了一个模板。)一方面,中岛敦告诫人们,为了人类文明,应该约束和控制我们的动物倾向:“我们所有人天生都是野兽。作为人类,我们的职责是像驯兽师控制他们的动物甚至教它们表演那样控制自己。”另一方面,诺伊・因塔农则以一位具有变形魔力的人,同时也是一位强大的高棉萨满的故事开启了《热带疾病》的“狂野”一半,而且开场方式与《正午显影》(用过两遍!)一模一样:“在很久以前······”
《正午显影》与《热带疾病》在童话故事方面的呼应似乎是更贴近的,因为在很多方面,《热带疾病》回归到了《正午显影》的那种纪实与幻想的融合以及每日的现实生活与奇幻的民间故事的融合,而且《正午显影》早已经在自己的故事链条接近最后的部分,即一群孩子讲一个关于“巫虎”的故事时为《热带疾病》的下半部分做好了准备。而《热带疾病》中那对老姐妹如果被放入《正午显影》讲故事的那个群体也会毫无违和感,她们给Keng 和Tong汽水、柚子、大麻,带他们参观神圣的洞穴和巨大的购物中心(这两个地方再次暗示了这部电影中乡村与城市、精神与商业的二元性)。第一个老妇人打扰了Keng和Tong这对恋人,想卖一些去寺庙时用的花给他们,她说:“如果你想得到福报,你就必须投资。”然后她就给他们讲了一个关于贪婪的故事。她从“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开始,这不由让我们想起了《正午显影》中的讲述者,然后《热带疾病》就开始了一段令人兴奋的离题,进入一个寓言故事:两个贪婪的农民遇到一个可以把石头神奇地变成金银的小和尚,但后来当他们被自己的贪婪所控制时,金银又都被变成了青蛙。(Keng、Tong和卖花女人还聊到一个贪婪的女人在《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中先是赢了很多钱,但最后只剩下3万泰铢的事,Keng说:“我连1万泰铢都挣不到,我多想遇见那个小和尚啊!”这些都回归到了《正午显影》里关于钱的主题。)跟《正午显影》一样,这部电影的前半部分,阿彼察邦在虚构中穿插了街头生活的真实片段,比如市场、交通、城市的喧闹、无意中拍到的人脸和身体等,还有就是用像纪录片的方式表现的工作的世界,尤其是对Tong切冰工作的表现具有一种幻觉般的现实主义效果。
与《正午显影》一样,《热带疾病》的前半部分虽然关注的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但仍旧强调了群体和群体性。这部电影的第一句台词就是“靠近点,集体合影!”,这是七名在边远的乡村地区巡逻的士兵围着Tommy的尸体(剧中没有透露尸体的身份)拍照时说的话,其中几位还想把照片给女朋友看,这像是诡异地预见了美国士兵在阿布格莱布监狱所拍摄的照片。阿彼察邦的目的是谴责士兵们的冷酷无情还是仅仅记录下他们对死亡漠不关心的态度呢?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个开场段落的气氛是戏谑的感觉,尽管面对很严重的情况,但大家仍在开玩笑。一个士兵追求着接线员,他在解释无线电对讲机里发出的噼噼啪啪的杂音时说:“这是我心中的静电,它在呼唤你”,“你像森林大火一样热辣和狂野”,而她则以爱情肥皂剧式的玩笑作为回应。后来音乐变为主题曲——泰国乐队“时尚秀”的极富感染力的歌曲《直接》,并接下来引出一个令人兴奋的推轨镜头,从而把场景转向了广阔的田野,这时音乐也随着镜头滑向茂密的草丛而从客观变为主观。接下来出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远景镜头,一个裸体男人像僵尸一样穿过树丛(我们要过很久之后才能意识到它是电影下半部分出现的那个忧郁的虎灵),这个镜头短暂地打破了故事的连续性,接着又恢复为士兵们在Tong乡下的家里停留和吃饭的镜头——近景景框里挤满了人。这时候,第二个群体、即Tong的家人替代了士兵们,他们在漆黑的夜里聚在露台的灯光下吃饭,而Tommy的尸体被包裹着挂在旁边的一棵树上,Tong迷信的父亲说尸体会在夜里膨胀然后变成幽灵。
在后来的一个段落中,当他们一起在外面看电视时,Tong的父亲建议Keng搬来帮他们经营农场;Tong的老母亲后来也加入进来,他们三个就那样静静地坐着,目光都望向同一个地方——右侧画外,像是一个短暂的小津式的沉思时刻。(电影的上半部分出现了大量的人造光源,即使在户外也是如此,比如挂在树上的荧光灯管以及阿彼察邦喜欢的灭蚊器的蓝光。还有就是交通环岛钟楼上的强照明灯,这也是阿彼察邦喜欢的东西。据导演说,这些人造灯光是这部电影的三位摄影指导之一——法国摄影师让-路易斯·维亚拉选择的。除此之外,这部电影看起来还像是被人物大量持续不断的微笑所散发出来的纯粹的喜悦从内部点燃了。)
Keng 和Tong 也都在群体中出现:Keng和他的战友们在一起;Tong则与他的家庭、同事、队友们在一起;他们也都与老妇人们在一起,或者在其他类似的社交场景比如电影院、台球厅、商场或者户外娱乐场所中出现。但Tong也有一些打破这个规律的独自的段落,比如因为他觉得军人制服对找工作有帮助,他就假扮成士兵去一家鞋店找工作(他的这种假扮军人行为可能暗示了他想与他的军人男友结合的欲望)。还有就是 Tong在找工作的间隙在一家餐馆吃鸡肉,阿彼察邦曾经强调说,那正是亚洲禽流感大流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要暗示这一点)。但正是用这两个男人在一起的热烈的场景,《热带疾病》表现出一种笼罩一切的、非常温柔的、难以言喻的幸福感。一些西方批评家认为,在传统环境下(家庭、村庄、寺庙、军队)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坚贞爱情显得非常令人不安,几乎是不可能的、理想化的东西,他们的爱情关系也难以被接受或者不被争议。但阿彼察邦只是简单地回应说,他对Tong 和Keng关系的描写是从记忆中提炼出来的(他说:“我们只保留了好的部分”),而那些浪漫的对话,比如Keng给Tong“Clash”乐队的磁带时说他把心也交给了Tong,这并不是一些批评家所说的“老套”或者令人厌烦的陈词滥调(clichéd),而是真实的、泰国人会在“甜言蜜语”的时刻彼此说的话。导演在筹划《热带疾病》的空闲时间,与同性恋行为艺术家迈克尔·沙万那塞合作了《铁娘子传奇》,这或许引发了他对男性之间爱情的新的热情。尽管有些批评家也提出了一些不那么令人信服的说法,比如《正午显影》中的男孩与他的外星朋友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同性恋,但阿彼察邦之前的电影中明确引入的同性恋欲望只有《祝福》中捎带着表现的Tommy 似乎不经意地勾引了一下Min的那一段。

在雨天或晴天、在大自然中或是在电影院、台球厅、医院、商场、大排档,在神圣的山洞以及艳俗花哨的露天餐厅里,Keng和Tong的浪漫故事轻松而愉快地上演着。在令人昏昏欲睡的夜车上,当Keng说自己“不希望没被人爱过就死去”时,Tong责怪他的想法“太愚蠢”,他们后来在路中间发现了Tong那条白色的老狗,送去检查之后发现它患上了癌症,这时候气氛变得很悲伤,但即使这种悲伤也是转瞬即逝的:Tong很快就得到了一条新的小狗,它有个引人注目的名字——“老虎”。(到目前为止,这段插曲无疑是阿彼察邦的又一个延伸到医院的段落。就像《祝福》中Min患有皮肤病是因为导演患过类似的病一样,这个事件也来自于真实生活:导演曾经养过一条狗,被诊断为癌症。这种念头与其说是记录式的,不如说更多的是日记式的,它来源于生活的日志。)
在视觉风格方面,《热带疾病》可以说详细阐释了阿彼察邦早期电影的视觉风格,运用了很多分析性剪辑2、重新构图、跟拍镜头、淡出、插入、微妙的变焦以及在感情强烈的相聚时刻所使用的引人注目的对角线构图,比如3Tong和Keng在倾盆大雨时在平台上避雨并聊着他们喜欢的泰国摇滚乐队“Clash”(常常被误认为英国的同名乐队)的时刻,又比如Keng面对虎灵的时刻:虎灵在画面左上角的树枝上,而士兵在画面右下角向上盯着它。[Keng 和 Tong 在卡车上的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镜头,让我们想起了《祝福》中Min和Roong开车去乡下约会的镜头。虽然有一组在公交车上的Tong与一个年轻女人密集的正反打镜头,那个女人一边用手机打着电话一边害羞地闪躲着目光,但这很快被证明是导演的一种误导:当Keng出现在反方向开来的一辆卡车上的时候,Tong 对那个女人的兴趣很快就转移到了Keng那里,那个女人被突然忽略(她也确实被放到画外了)强调了 Tong 的真情所在。

《热带疾病》所表现的甜蜜时光在形式上是轻松随意的,比如偶然的题外之物、无意间瞥见的东西、快乐的意外事件等:当Tong大步穿过夜晚的城市街道时经过了一张《雨夜逃夫》(One Night Husband,2003年)的海报,这是阿彼察邦最喜欢的泰国电影之一,还瞥见一只把爪子伸给主人的大狗,这也是这部电影众多的关于狗的镜头之一(在这方面,阿彼察邦简直可以与阿基·考里斯马基一较高下了)。在台球厅里,摄像机捕捉到一个年轻女孩全神贯注准备打台球的样子,然后又停留在一个半靠半躺在椅子上、心不在焉的年轻男孩身上,阿彼察邦说选择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天使般的面容。按照他的习惯做法,阿彼察邦把两段非常泰国式的媚俗场面加入了Tong 和Keng的爱情故事中:一段是在大排档的舞台上唱歌,一段是由Keng在电影院的洗手间里碰见的那个对他露出灿烂笑容的男子领衔的、电子音乐伴奏下的广场健身操。(后来紧接着的是一个紧凑的对角线构图的镜头,拍摄晚上在河岸边休闲躺坐着的人们,这个“多余”的集体休闲的画面让我们联想起了之前的那个Keng与Tong的父母在一起的画面。)这段音乐插曲唤起了阿彼察邦对当地流行音乐的热情,比如loog-thung这种有着令人腻烦的转音的泰国民间音乐。在他第一次为这个歌唱段落勘景的时候,阿彼察邦就发现了这个深深打动他的地方,后来这个餐馆因为翻修抹去了它那些俗气的华丽景致,包括那些令人炫目的闪光亮片、彩带、圆点还有那些流行的颜色,阿彼察邦又让餐馆老板重新恢复了它们。“虽然我老了,但请把我想象成年轻的妹妹”,随着这句话而来的是一个带着“美式舞台”风格的老年女歌手,她像一个野兽派的人物,裹着紫罗兰色的长礼服,红色的带着亮片的披肩上装饰着一朵艳丽的绿玫瑰,两个笨拙的伴舞者在她后面慢慢地扭来扭去。她唱的第二首歌Wana Sawat,虽然英文版本中没有显示歌词,但这首歌其实是关于一对恋人在丛林中寻找浪漫约会的地方的,这看来并不是巧合,而是这部电影的上半部分为下半部分所做的众多准备之一。令人赞叹的是,虽然这部分因为演唱者缺乏表演经验而用了超过五十个镜头来拍摄,但表现出来的结果却像是没有那么大的工作量,带给我们的感觉是清新和轻快的,像是飘荡在民间音乐会的天堂中。

作为导演自己的一个私人“麦高芬”4田,把《祝福》中Tommy 的尸体放在《热带疾病》的开头的这种结合被阿彼察邦解释为“这是我的一点自娱自乐”5。(考虑到在上半部的最后还给了在卡车上装扮成士兵的阿彼察邦一个很短的镜头,这个希区柯克式的引用也不算太令人意外。)阿彼察邦的很多美学上的选择都依赖于他的直觉,即对于他自己和他的观众而言,什么才是快乐的。比如当被问到他为什么给 Tong 选择了冰冷的切冰工作时,阿彼察邦说他自己也“并不确定”,但因为影片的拍摄现场太炎热了,他想加点冷的东西作为对比。这个简单、本能的选择却成就了《热带疾病》中一些最动人的影像,这是阿彼察邦电影中把日常平淡无奇的事物通过专注的凝视升华到超现实主义的最好的例子之一:影像之细致与声音的现实主义(切,削,锯嗡嗡声)把可以独立存在的、充满诗意的、尤里斯·伊文思式的工业纪录片转化为某种梦幻般的东西,最终结束于一个阿彼察邦所独有的那种模糊的缝合镜头。Tong的目光从手头工作中移开,朝银幕外的我们看过来,接下来的镜头是一个缓慢向前的推轨镜头,镜头中是一个俯瞰湖面的天鹅雕塑。这个剪辑似乎暗示了Tong 是从他所在的制冰工厂看到这个天鹅的身影的,这显然不太可能,不过人们还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式“解释”这个天鹅,比如因为冰雕的天鹅常常被用于婚宴装饰,所以这个剪辑还可以看作工业领域与神秘、媚俗的琐事的一种结合,用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镜头转换完成了升华;或者说是对《祝福》的人造与自然主题的重复,在这里,人造的天鹅与我们在上半部分其他地方看到的许多养殖的动物一起代表着驯养或者文明,与下半部分丛林中的野生动物形成对比。相反的,也有人猜测这只天鹅只是阿彼察邦当时凭感觉的“误拍”而已,“作为他自娱自乐的一个小动作”,后来(很明智地)用来替换掉Tong因为惹恼老板娘而被解雇的段落。诗意胜过了镜头本身的逻辑:导演把他喜欢的东西放进去,省略掉别人觉得重要的东西。

Keng 和 Tong 的爱情天堂里也有着《祝福》的那种亲密感,但跟Min和Roong一样,它也同样是暂时的,并没有摆脱死亡和暴力的底色。从一开始让他们相遇的谋杀到Keng提到偷伐木材的黑社会对他不满,从狗得了癌症到Tong粗暴地拒绝解释Keng问到的他的伤口,从他们探访神圣的山洞以Keng害怕有毒气而匆匆结束,到Noi的姐姐说她和她丈夫的“丛林爱情故事”充满了疟疾的回忆,人物似乎不断地意识到疾病、敌意和死亡。(这个有着光点和毒气的山洞的创意显然是来源于阿彼察邦的另一个作品,也是对于废弃的电影院和密 室的回忆——《黑暗中的鬼魂》)Tong 和Keng“吞噬”着彼此,Keng摩擦、细嗅、吻着、搓着Tong可能刚被小便溅湿的手,而Tong 则回应以饥渴地舔着Keng的手,他们似乎要吞掉对方的性意味和动物性的回归都是为了他们在电影下半部原始的结合而做的准备。接下来,Keng开启了一场兴高采烈的《夜幕降临》6式的摩托车之旅:伴随着《小房间》(Small Room)的音乐,路灯像飞碟(UFO)一样在头顶闪过,一伙年轻人正在路边殴打一个倒在地上的人。这伙人似乎注意到了摄像机,然后开始愤怒地追赶,街头暴力驱散了爱情幻梦(这个场景看起来像是偶然拍到的,但实际上是表演的)。
就像电影一开始的那样,士兵们又聚集在镜头里,Keng随着他们去乡下了。(镜头划过时我们可以瞥见阿彼察邦穿着军装坐在皮卡车上。就像Tong穿着军装假扮军人去找工作一样,阿彼察邦在这里也扮演了一个士兵。)一个突然的剪切把我们从尘土飞扬的路上扔到一个安静的卧室里,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田园风光。阿彼察邦曾经说摄影师希望在这个寂静的、光线充足的空间里实现维米尔式的画面,尽管维米尔式画面的光线一般来自画框的左边,而不是像这里来自正面的大窗户。Tong醒了,起身坐着,看着外面的世界(这又是一个阿彼察邦把内部和外部世界通过沉思融为一体的时刻),接着他离开了卧室。然后在一个手持跟拍的镜头中,Keng来到了卧室里,他把手放在床垫上感受刚刚离开的Tong的体温,在画外音中,一个老女人带来的让人惊恐的消息打破了这份充满情欲的宁静:“我今早发现了一个爪印,一头牛不见了。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晚上了,所有的村民都吓得要死。一定是个怪物!”当Keng看着Tong以前照片的时候,通过提到捕食牛的“怪兽”以及闪烁后被黑暗吞噬的银幕,《热带疾病》上半部分充满情欲的、怀旧的气氛终于被黑暗吞没了,无论是字面上还是比喻上都是如此。

在持续数秒的、令人不安的黑暗中,这部电影重生了,虽然看起来与上半部完全不同,但其实是一样的。其他的电影有的用“重新开始”作为一种观念性的玩笑(大岛渚的《三个复活的醉汉》),有的用它作为超现实主义的打破因果逻辑的方式(林奇的《穆赫兰道》),又或者用它作为一种激进的构造方式:比如戈达尔的最后一部杰作——《爱的挽歌》就分为两个时期、两个互相关联的故事以及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觉方案,它从源自普雷明格的《你好,忧愁!》的“时间色彩”(temporal-colour)模式开始,上半部分以明亮的黑白胶片拍摄,把巴黎拍得令人倍感忧郁,它那些在明信片上庄严而闪亮的、标志性的历史遗迹看起来却像是在嘲笑纪念的意义。而它的下半部分则是自然世界,这种自然世界在戈达尔晚期的“超验”电影中给了观众一种喘息、甚至可以说是被拯救的机会。下半部开始于波涛汹涌的大海和布列塔尼海岸,被渲染成为硫黄的橙色、有毒的蓝色、瘟疫式的黄色所组成的数字影像大火。导演似乎在宣称,在这个“短期记忆”7的世界里,历史和文化都呈现为数字影像那样的荒诞摇摆、虚幻不定的样貌。
阿彼察邦让电影从中间断裂的做法也同样包含了戈达尔那种城市与自然世界的区分以及视觉方案上的差异,尽管后者并没有戈达尔的电影所表现的那么明显。在中间断裂之后,阿彼察邦从维米尔风格转向了亨利·卢梭风格,并且为了追求一种更原始的风格以与他的民间神话故事相匹配,他的第二个故事穿插了字幕,还有刻意找来的野生、怪诞动物的原始绘画用来表示洞穴岩画或者泰国图腾,这些都类似于默片的做法。尽管偶尔会使用缓慢的推拉镜头,“灵魂之路”比上半部分更依赖于静止镜头,正如阿彼察邦在DVD的解说中所承认的,部分原因是他“不太擅长手持拍摄”(手持拍摄的大部分备用镜头都被弃用了)。在上半部分明显使用人工光源的情况下,“灵魂之路”则只使用了自然光,所以突然变得非常模糊。在这里,难以分辨就成了不祥的预兆。“不显示出来是最好的选择,”阿彼察邦说,“因为它们都跟大脑中的东西有关。”这让他听起来像是晚年的雅克·图尔尼尔。这些常常让人感到难以穿透的黑暗影像被伴以混合的声音,这些声音将电子音效与大量的丛林声音混合在一起,用导演的话说就是使得音源“难以辨认,模棱两可,神秘莫测”。(为了收集奇异而真实的声音片段,本片的声音指导在晚上非法进入丛林,还遇到了一只熊和一群大象。)在这个模糊、难以捉摸、听不见、看不清的幽冥世界里,遥远的动物的哀鸣可能是来自被老虎捕食的牛,又或者是来自赤身裸体的鬼魂哭着穿过丛林时的哀嚎,就像狒狒所描述的那样:“他的灵魂饥饿又孤独”。

虎灵到底是护林队员的情侣还是他的猎物?它是想跟他做爱还是想消灭他?它们是同一种生灵吗?“士兵!”那个好说教的狒狒对着护林队员喊道,“那只老虎像影子一样尾随着你···我看到你是他的猎物和同伴,他在远处的山上就能闻到你的气味,而你很快也会有相同的感觉。杀了他,把他从魔鬼的世界中解救出来。或者让他吞噬你,你进入他的世界。”
虽然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那篇精彩的关于《热带疾病》在当地反响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影片的第二部分根植于古老的泰国文化,它“属于”古老的泰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关于”它的,我们却仍可以把“灵魂之路”看作奥维德和俄耳甫斯的结合:这是爱情与变形的故事,一个人必须进入地狱去救回他的爱人,把他从“魔鬼世界”中解救出来,结果却发现他自己也变成了另一种生物。“每个人都会杀死他所爱的东西”,这里表现出来的是士兵(也许是Keng)追赶虎灵(也许是变身的Tong),虎灵与他激烈搏斗,然后把士兵扔下悬崖,像恐怖片里那样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士兵一直在试图射杀那个猎物,最终却只是射中了一头牛,牛的身体还在喘息起伏着,也许追踪者比他所追踪的猎物杀的牛还多。最终当鬼魂变成了一只真正的老虎时,镜头像是从正面拍摄的透视画,它用发亮的眼睛催眠了那个发抖的追踪者,老虎燃烧着的光芒和被惊呆了的注视者合成为一个奇妙的遮摄镜头,所有的人兽争斗或结合的问题在这时都暂停了(导演删掉了表现士兵充满情欲地爱抚着老虎的段落),然后字幕显示:“怪兽,我会给你我的灵魂,我的肉体,还有我的记忆。”影像中是士兵泪流满面的恐惧的脸,这表示追踪者已经向他的猎物投降了,接着老虎宣告:“我的每一滴血都在唱着我们的歌,一首快乐之歌,你,听到了吗?”这些都暗示了分裂与交融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老虎可能突袭,士兵也可能射击,但在那模糊的最后一声枪响中,在漆黑夜空下的树木沙沙作响中,在永恒的终止面前,猎人和猎物都不复存在了。

阿彼察邦把《热带疾病》中间的断裂描述为制造“泰国(非同卵)双胞胎”的过程,或者更严肃的说法是“从中间倒映出两边的一面镜子”8,引诱和促使人们把两部分看成是彼此的变体,从而列举它们之间的呼应和类似之处。如果士兵和虎灵的扮演者不同于上半部分的Keng 和 Tong的扮演者,那么这种诱惑就会减弱,但班罗普·洛罗伊和萨卡达·卡温巴迪这两位演员的重复出现,特别是前者的角色与Keng完全一致(泰国的士兵有时候会承担护林队员的工作),以及精心安排的比如电影开场部分的对讲机在下半部分丛林中被毁坏的细节,还有上半部分结尾那个老妇人讲的关于捕食牛的怪兽故事也被转到了下半部分,所有这一切都强烈地暗示着连续性。另一些对应关系也许可以从阿彼察邦自己的评论中找到:被他称为“小天使”的丛林萤火虫是不是上半部分台球厅里沉睡的“天使”的重现?9下半部分护林队员用来与野兽“沟通”的木牛铃是否可以作为开场部分狂风中的无线电台的古老对应物?(木牛铃在字幕中被称为“士兵的神秘声音设备”,它也许预示了护林队员的无线电将会失灵。)
在上下两部分中寻找相同之处也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会强加一些严格的相似性到一部毕竟是阿彼察邦的电影身上,而它常常是充满了偶然的。而且导演似乎下决心要破坏对叙事的任何系统性的、条理性的把握,例如在下半部的一开始和最后的一系列镜头中都插入了一个简短但又令人迷惑不解的护林队员戴着黑色头套的镜头,这打破了真实、想象、幻觉、梦境之间所有的分界线。除了不确定性之外,阿彼察邦还强调了回忆的重要性,这种最难以言传的、不稳定的能力,却是理解上下两个故事以及两个情侣之间的共生关系的关键:“即便故事以线性结构呈现,但《热带疾病》仍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然而这两个世界可以被人物(观众可以理解为相同或者不同的人物)连接起来。最关键的是记忆,上半部分的记忆验证了下半部分,就像下半部分也反过来验证了上半部分一样,两部分缺一不可。”10
“怪兽···”老虎无意中夸张地模仿着圣餐仪式的口吻对士兵说,“我会给你我的灵魂,我的肉体,还有我的记忆。”虽然阿彼察邦经常强调他的电影是有关记忆的负担的,但大家很少会把阿彼察邦看作拍摄记忆的导演,至少不像大家看待阿伦·雷乃、克里斯·马克或者王家卫那样。认识这部电影的上下两部分的模式当然还得依赖于记忆,但导演的头脑中有比记忆更深刻的东西。《热带疾病》中到处都是记忆的标记(比如Tong的照片,它们既是虚构故事中他与其他男人之间私情的纪念,也是演员自己的真实生活的留念),以及让我们想起从前的电影和电影类型的东西,还有借鉴泰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正如我们提到过的,《热带疾病》在很多方面都重复着《正午显影》,也重复着很多《祝福》中的影像、人物、事物和地点,当然还有它的二元结构、它的医院的段落、它的令人不安的爱情以及对丛林时间的弱化。这也正如阿彼察邦所说的:“我希望重访一个地方,然后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它”,(然而,相比《祝福》的第一部分的时间是压缩和线性的,《热带疾病》的时间范围则是不确定的,很难弄清每个事件之间到底经过了多少时间。)更广泛地说,就像《正午显影》是作为对民族叙事方式的纪念一样,从诺伊·因塔农的探险故事到让人联想起流行的鬼怪电影的这部电影的泰文片名——《怪兽》(Sud Pralad),以及下半部分开始时在寺庙的墙壁上再现古老叙事方式的原始图画(因为图画在这类神圣的地方不容易被破坏),《热带疾病》引用了以上众多的泰国传统文化元素,使得它成为对过去或者消失的文明的一种纪念。
或许按照这个思路,英文片名中的“疾病”并不是疾病、单相思或者“疯狂的爱”(amour fou),而是关于回忆的疾病:“我们总会在人生的某个时刻被我们对爱人的美好回忆所窒息。”阿彼察邦说,“《热带疾病》中的恋人就是为爱窒息,因为他们的爱是如此完美、如此自然!”11

- 译者注:Daisy chain,这里意指首尾相连。 ↩︎
- 译者注:Analytical Editing,分析性剪辑,指在同一个场景内切到某个部分用以强化表现细节的剪辑方式。 ↩︎
- 译者注:原文误作“右上角”和“左下角”,译文已更正。 ↩︎
- 译者注:MacGuffin,可以理解为象征物。这个词是由英国编剧安格斯·麦克菲尔(Angus MacPhail)创造的,并在20世纪30年代因为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和他的电影而普及开来。 ↩︎
- Most of Joe's comments about the film derive from his commentary on the Strand Releasing DVD. ↩︎
- 译者注:Here Comes The Night,20世纪60年代著名英文歌曲。 ↩︎
- 译者注:这里引用的是戈达尔的电影名,《短期记忆》(La mémoire courte, 1979年)。 ↩︎
- James Quandt, "Exquisite Corpus," op.cit.
↩︎ - 这似乎无意中证实了凯伦·纽曼所观察到的阿彼察邦对本土文化消亡的关注。泰国萤火虫已经成为一个濒危物种,根据最近的新闻报道:“随着人类开发范围的扩大,在全世界范围内,其栖息地环境都变得恶化,或者遭到破坏以及碎片化。泰国渔民过去借助萤火虫发出的光在夜间工作,而现在萤火虫正迅速从当地生物圈消失。见 Seth Mydans,“Talking to Fireflies Before Their Flash Disappears.”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2008,P. A20 ↩︎
- Press kit for Tropical Malady.
↩︎ - Ibi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