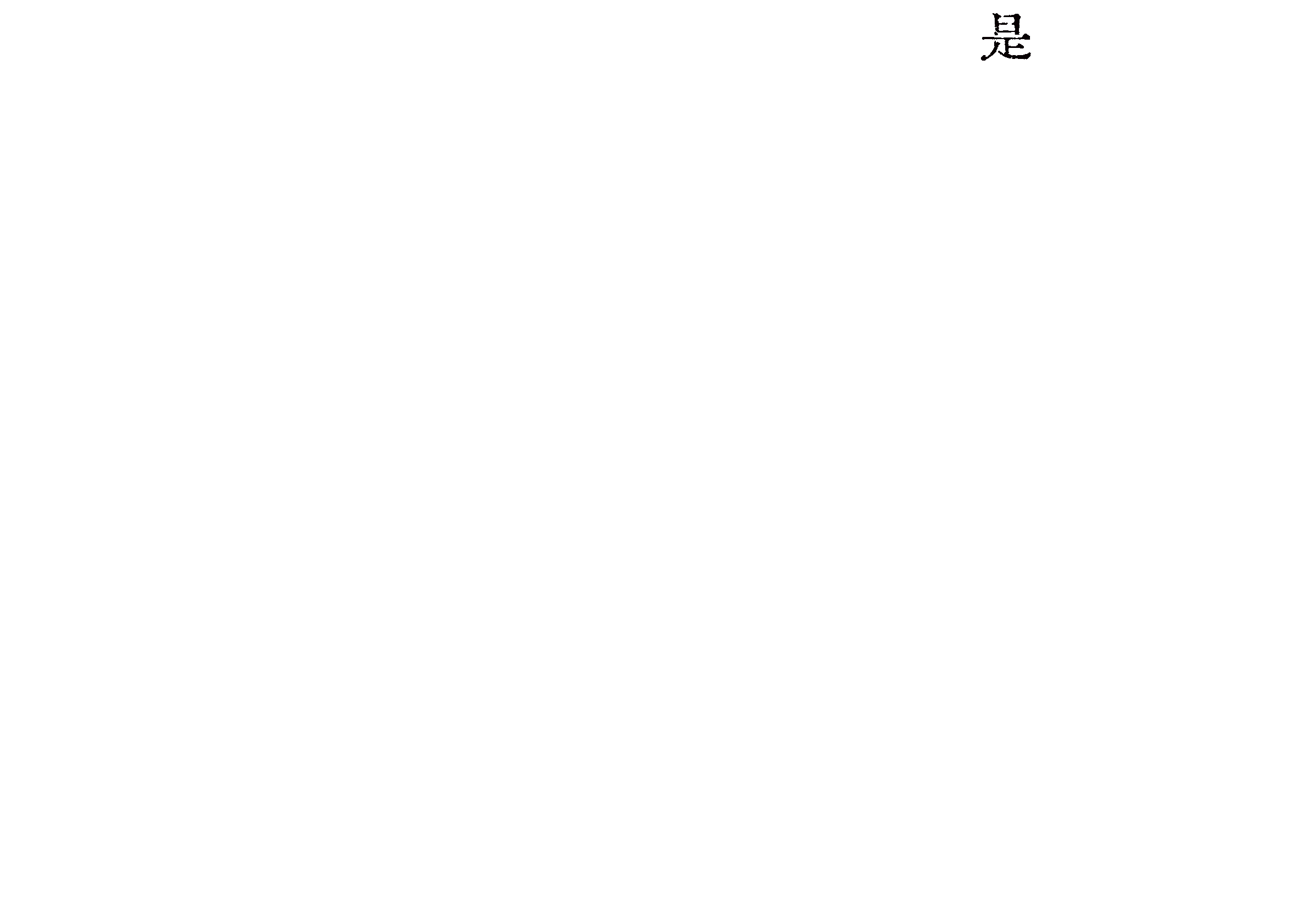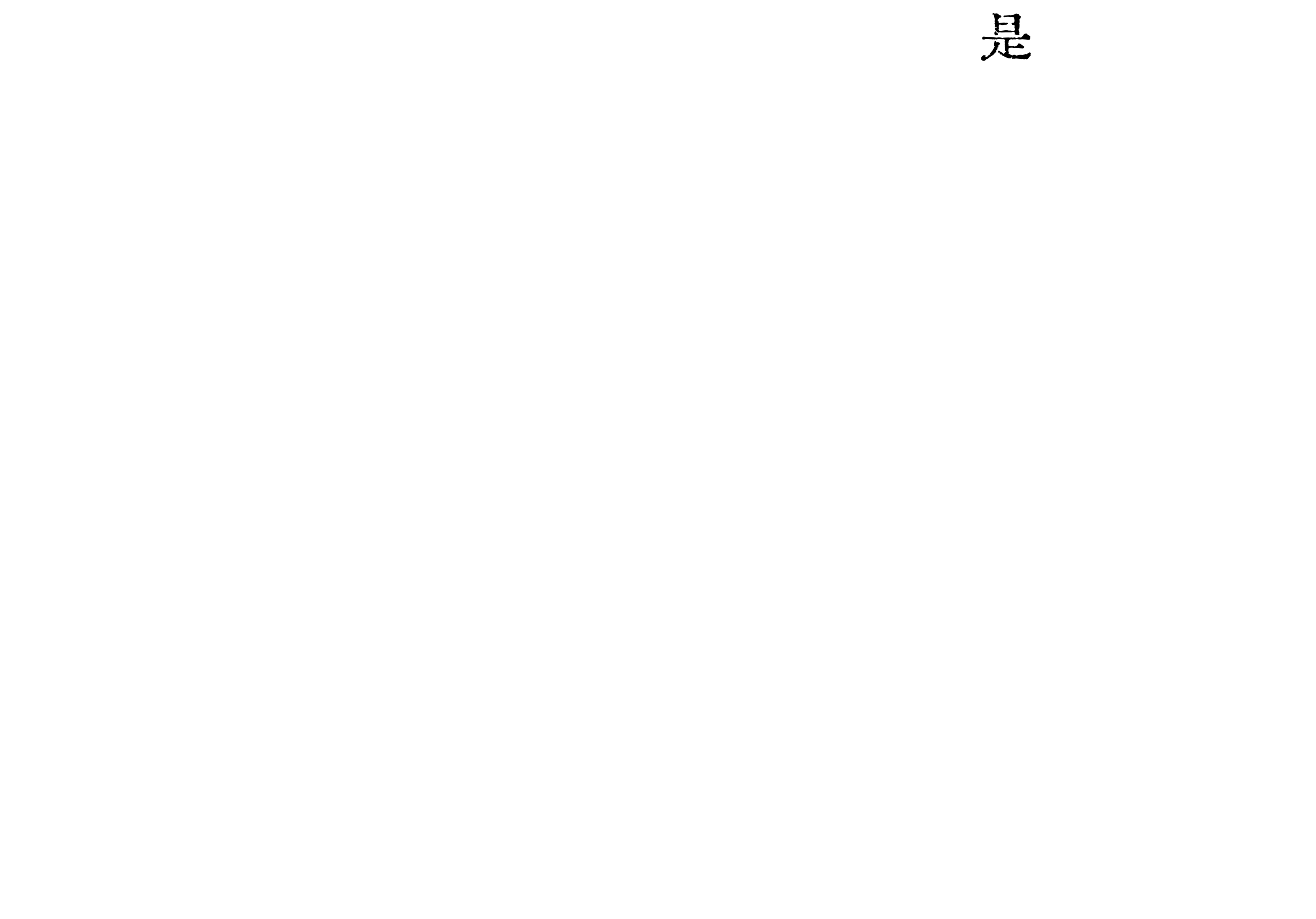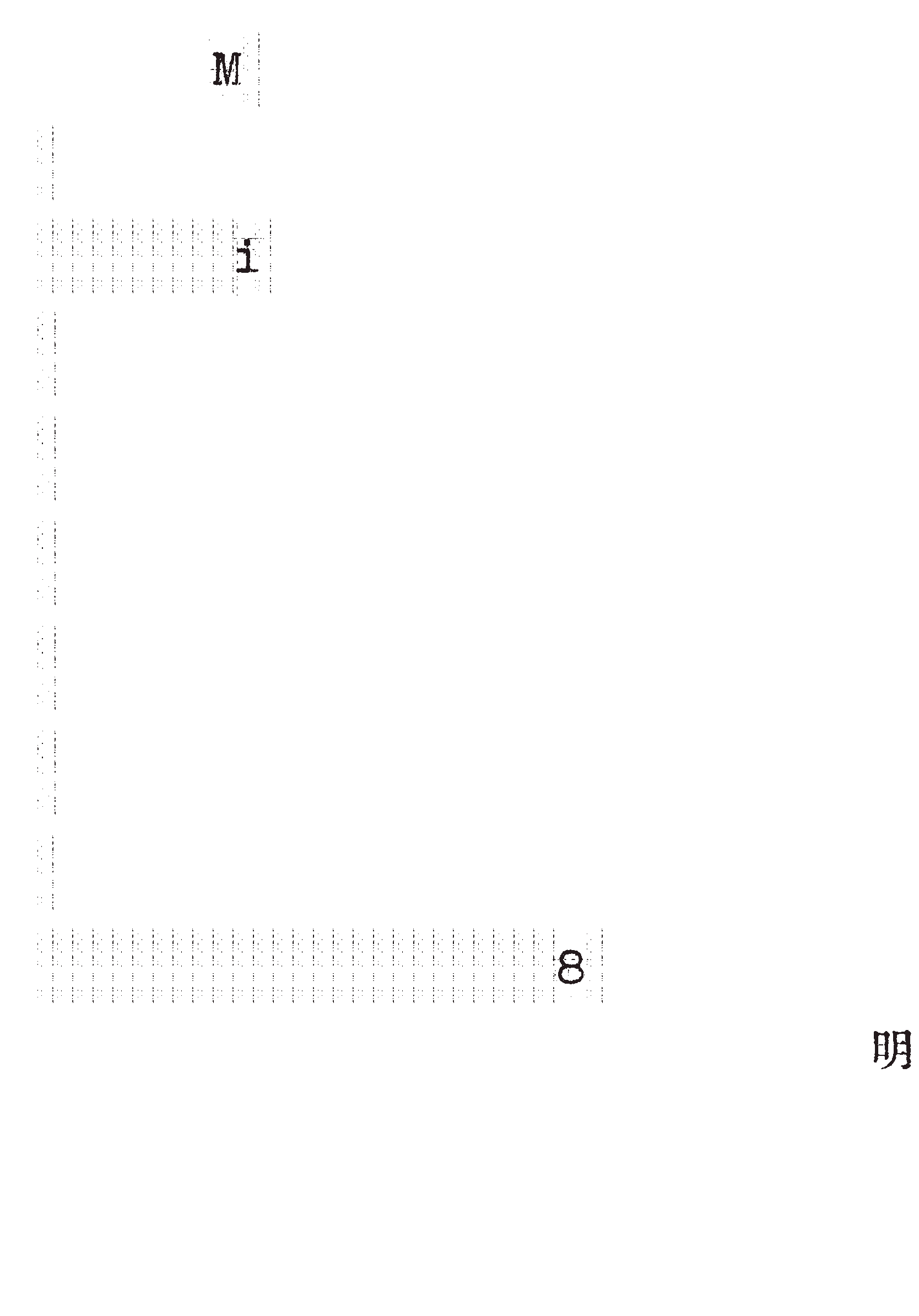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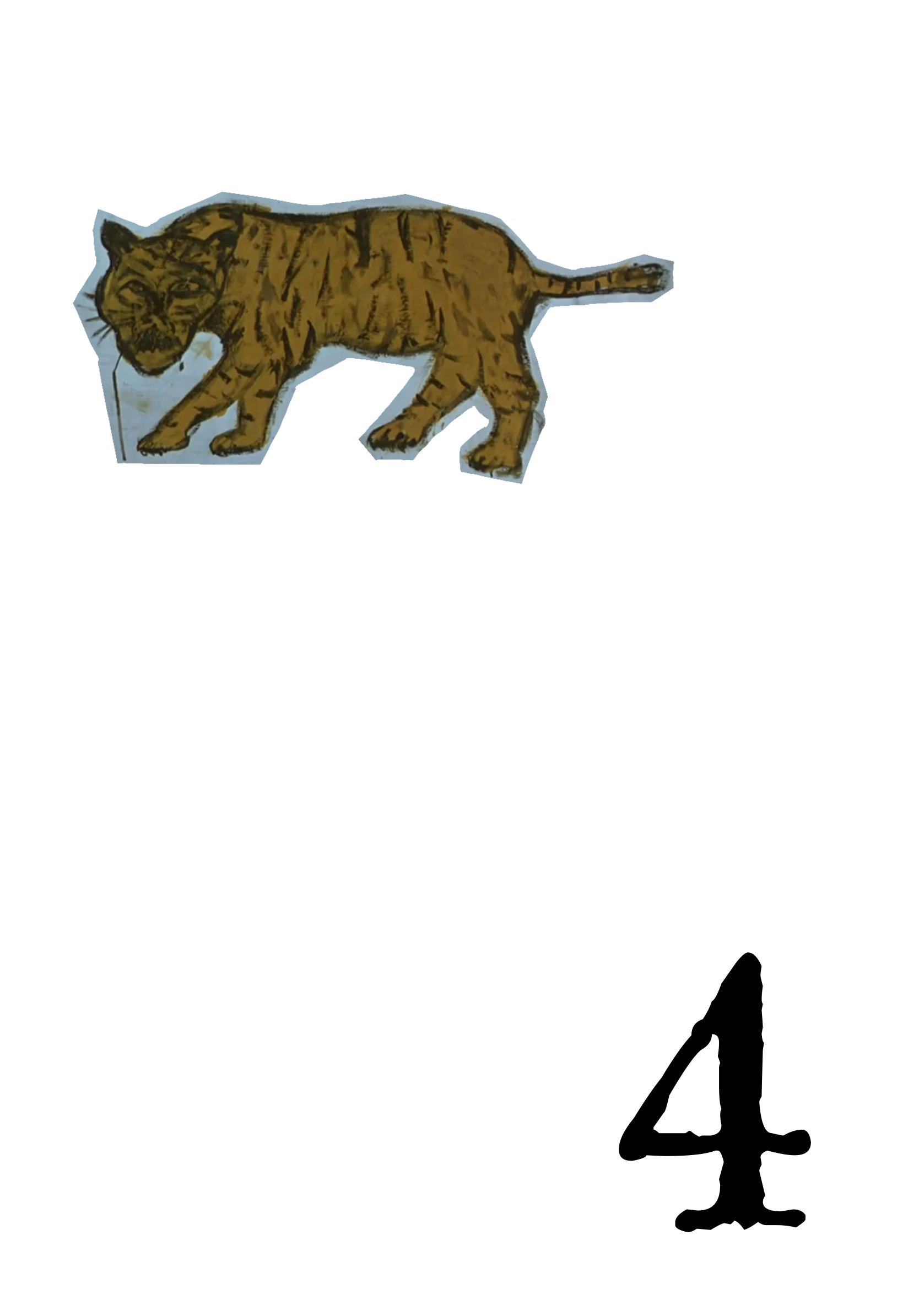
前段时间,我们和明德的朋友们一起看了《热带疾病》这部电影:

父母都为医生的阿彼察邦,对孔敬小城的医院有着独特的记忆。这不仅体现在他电影中时而暖黄时而青蓝的医院场景中,这些经历亦构成了他作品的一个明显线索:在片名或情节里,综合症、疾病这样的概念像热带季风般挥之不去。而 “热带疾病”(Tropical Malady) 就是其中一个标记。
身体的疾病折磨肉体,而精神疾病折磨尚未开悟的人。对于阿彼察邦来说,这两者或许无法分割。所以他说,“拍电影就像唤醒死者,然后给他们一个新的灵魂让他们再次行走。”
此前我总是担心,谈论阿彼察邦的电影,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会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批评的困境,妄图通过一些相似性的累积来描述无法言喻的东西。
事实的相反的,我想,《热带疾病》多多少少地激起了在场的各位对回忆的渴望,凭着阿彼察邦的影像机制,各自又彼此地获得了对普遍之物的另一种特别的审视。直到现在,我还会偶然拾得当时那些被重述的、即兴的记忆和语词,山林的夜爬,摩托车驶向灯火未烬的寺庙…
对话:该隐、Sharon、子元、阿羡、观其妙、阿伟、小田、youkee…
看起来,这部电影的前后两个部分是割裂的。我觉得,回忆是连接两者的媒介。就好像是,Keng 盯着 Tong 的照片,然后开启了一场回忆。或者说,他被一只名叫“记忆”的猛兽攻击了,迫使他踏入另一个旅程。
影片后半段有一句台词,虎灵“是一个生命只存在于别人记忆中的生物”。寻找虎灵,就是 Keng 在回忆中找寻自己的欲望的过程。

我更觉得,后半段像是士兵进入了梦境。是的,他自己就像是这个故事中的虎灵一样,进入另一个身体,作为士兵或者是护林员的他,去另一个世界狩猎。我们还记得这样的场景,当影片里是戴上了黑色面罩的 Keng (假设我们认为那是 Keng 的话)在夜晚睡着后,又好似进入了另一层梦境,并从中醒来,看到另外一个自己。他在追逐什么,可能是那只老虎,他在地上爬行。
如果说所谓的虎灵是他恋人 Tong 的化身,最开始的他是猎手,虎灵是猎物。那么随着梦境的推进,他反到变成了猎物,被欲望追赶。片中说,“老虎的灵魂是孤独的”,老虎也渴望着士兵,循着他的气味,想要找到他。
两者的角色、身份不断地流转。就像片中后来的 Keng 发现,是自己杀死了那头牛(而在此前的情节里正是这头牛的失踪开启了士兵的丛林之旅)后,他开始爬行,从人类变成了野兽。而后当他抬头,被树上的老虎凝视,二者的角色又发生的颠倒。


阿彼察邦很喜欢在引入叙事中的寓言,在之后将其发展成真实的情节,以此模糊虚构与真实的边界。我记得在《正午显影》和《幻梦墓园》里也是如此。从真实步入虚幻,我觉得这是阿彼察邦的故事迷人的地方。
观看的过程中,我一度很恍惚,因为些许感觉让我想起之前夜爬的经历。比如那些拿手电筒照着藤蔓的镜头。有时你可能会重走旧路,或者误闯入荒山里的墓地。甚至会开点小差,漫无目的地游走。
夜晚本身就是危险的,当事物不可见,听到的声音也不知所是的时候,更容易产生各种幻觉不是吗。如果有一个夜爬的伙伴,那在沉默的间隙也总会感觉不安,拿对方当陌生人一般,一种不寻常的感觉便涌现出来。
我也想到了一次夜间的经历,我和朋友骑摩托车上山,山路的尽头伫立着一座寺庙。寺庙的广播里还在诵经祈福。我们走了进去,隐约瞥见烛台的微光,但是没看到人影。
刚讲到我们夜爬是对森林的恐惧,我想到一个做东南亚研究的学者,在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到各地去做访问调查,他就采访了一个印度尼西亚的在丛林中生活的朋友。这个朋友说,《热带疾病》对他来说很好懂,并且能感受到里面的各种细节,后半段的丛林故事,就和自己在丛林里的经历一样,他可以辨识出里面的声音是哪些动物的叫声。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可能,阿彼察邦只是在还原自己对丛林的记忆和感觉,只是我们没有此类经历的人,看到后会觉得很神秘、很奇异?

大家觉得,后半段的这段独白“我在这里看见我自己、我妈妈、我爸爸,恐惧、悲伤,一切都那么的真实,他们把我带回现实…” 是谁的独白呢?
我的看法是,电影里有两套逻辑:要么“杀死对方,把他从灵界解放”,让他解脱;或者献祭自己,让他吞噬你, 进入他的世界,从而成为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个逻辑是,恶灵只有在别人的记忆中才存在;另一个逻辑是,恶灵将把那个人吃掉,而此人的信息/记忆被恶灵所占据。
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出独白的主体是那个“可以吞噬对方者”的声音,在影片中就是虎灵。我们要知道,片中的老虎不是老虎,它是可以幻化成各种东西的一个灵。很多镜头在反复强调它的脚印是不一样的。乃因着 Keng 对 Tong 的执念,他才把虎灵对象化为了 Tong 的形象。

到此为止,我们往往可以在阿彼察邦的电影里看到所谓“双”的结构,而两个东西之间互相关联。我觉得,这部电影的前半部分,始终在为后半部分做准备,让我们明白第二个故事所讲述的是什么。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阿彼察邦在西方这么受欢迎,因为他的影片展现的是非西方的逻辑——非理逻辑,西方视角下东方人特有的“逻辑”。没有逻辑的事物之间彼此关联,这在后现代的语境里是非常令人着迷的。
阿彼察邦的电影里,事物总是普遍联系的,甚至可以跨越物质和灵魂。如果说是一种逻辑的话,那就是旨在让潜在的因素互相关联。这种关联与循环交替基于佛教的整体思维和万物一体的观念,而非更接近西方理性。就像刚刚说的回溯性理解那头被杀死的牛,体现的即是佛家所说的因与果的关系。万物之间都有可能生发机缘,制造因果。而你以为看到的因,其实是果,在另一个角度果又成为了因。

我觉得这部电影前面展现那么多两人相处的日常、比较现实的部分,达到了一定的情感浓度,就为后面更深层欲望的融合做了足够的铺垫,能够让人产生比较强烈的情感认同。
我看的时候,会带入阿彼察邦个人的身份,我更想知道导演是怎么展现欲望的,那肯定和他自己的生命经验有关系。这个电影从比较浅显的层面来看讲的是一对同性恋人的故事,而前后两部分是关于同性欲望的两面性的对照,前一部分是快乐、欢愉的一面。而当我们看到后半部分的时候,再回想两人的相处,就会发现一些很创伤或者暴力的东西已经存在。这样,欲望从积极变得些许消极?我想我们每个人看完后半部分都会感受到一种痛苦,这种痛苦不单是作为一种同性恋身份的边缘化的痛苦,而是每个人潜在的欲望被揭示出来的痛苦,或者说追寻欲望踪迹的痛苦。而酷儿的欲望更加消解、也更加普遍,身份的流动时刻发生。

影片的前半部分在我看来是非常天真、自然的,它恰恰是泰国文化的一种特性,未显示出东亚国家的那种强大的父权压迫。片中的父母、邻里都是很天然的对待 Keng 和 Tong。
我觉得这不能代表泰国的一种文化特性,它只是表现出了一种去男性中心、以女性的经济能力为中心、男同性恋围绕在这些女性周围的理想中的环境。

我反倒觉得女性的位置在这里并没有着重强调,始终都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感生发。一开始 Tong 对着同车的女生笑,这种笑没有受到二元的、异性恋框架的制约,很明显,下一个镜头 Tong 对 Keng 投向的笑容加强了这种自然性。接下来,去描绘 Tong 和 Keng 这种趋向于亲密的关系,导演用了很多肉身的、气味的元素。在游玩后即将分别的一幕里,混合着小便的气味,Tong 舔舐着 Keng 的手,这里即将要引入后半段叙事,动物性已经呼之欲出。正如影片开篇就说,“我们的天性都是疯狂野兽”。
野兽是双面的,一面是天真,一切在自然中生发,爱就是这样产生的,无关男女;另一面就是后半段给我们揭示的东西了。



在这样的结构里,Keng 的位置相对没有变化,或者说是在后半部分踏足自己欲望的深处去。但是 Tong 在前半部分相对来说是被动的、温和的、天真的、惹人怜爱的形象,但在后半部分,他变成了一个有很多佛教纹身加持的,既不是人类也不是动物的东西。纹身者与野兽的双重化身,都突显了这种欲望的不可触达性。我的意思是,前面的故事看起来仍是两个人交融在一起,但后面的 Tong 就是用纹身把自己武装起来,就像用一种首先伤害自己的方式来拒绝别人的进入、触碰。
彼时我们才知道,愉快、轻松的氛围可能是个假象,终点是对个人痛苦的严肃描绘。
就如其中一句独白,“怪物,给你我的灵,我的肉,和我的回忆,我的每一滴血,都唱着我们的歌”,我会觉得这是一种朝向死亡、毁灭的欲望。

我觉得,爱情的欲望和对死亡的欲望紧密相连。而同性之间则会潜藏着更多的暴力和冲突。我甚至觉得,一种同性情欲流动在影片不同的角色之间。
前半部分看似是一种泰国“小清新”式的感情刻画,看到后面,仿佛在梦境中进入了这种感情的阴面,潜在的伤害正在发生。这种感情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复杂,且不明晰。


影片前面以同性恋人的故事为起点,后面已不再强调这两个男人之间的故事了。而是落到一种普遍的欲望中,人和人,人和野兽,甚至是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
对于这个村庄,作为士兵的 Keng 可能是个外来者、闯入者,而 Tong 是这里土生土长的青年。我们看到的是,外来者是如何打破一些东西,融入这里。被吞噬、被吃掉也好,Keng 始终是融入到这个“自然”里,被同化成为这里的一部分。这让我想到了我在泰国游玩的感受,不知不觉就融入当地了。

后记
在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支持的独裁统治时期,阿彼察邦的家乡孔敬所在的东北部贫困地区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真正泰国的标志。时到如今,我们基于各种媒介所见到的泰国,可能与阿彼察邦镜头中的非城市社会结构相距得更远。他的电影,更像从孔敬的“内部”自然生发而出,而不只是“关于”。
观看《热带疾病》,是一种对精神或情感恶疾的治疗。又仿佛因我们承担了某种共患,灾难有所减轻。一种幸福的受难,“对被动性的感同身受,对痛苦的感同身受,对温柔的那种消隐的感同身受”,在那一晚的记忆之场中流转。
在没有终点的途中往复循环,这一过程时刻提醒着自身的无能。无能的疾病,不再是对陨落之物的怀乡,而是那个陨落的“世界”尚未且永远不会到来。若在未曾踏至的土地上妄结出记念的果实,那虎灵伸出的长舌与士兵颤栗的屈服就只可能是一种平行的姿势。如何用你那记忆的幽灵填补那片尚未存在的丛林呢,正是它慷慨地滋养了我们。分别后的镜头扫过城乡黏腻的街景,在车尾扬起尘烟,你我消失在幻象的帷幕,而大地长久地向前推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