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这是发表于2006年7月 Sinlapawatthanatham 杂志泰语版第140-153页文章的扩展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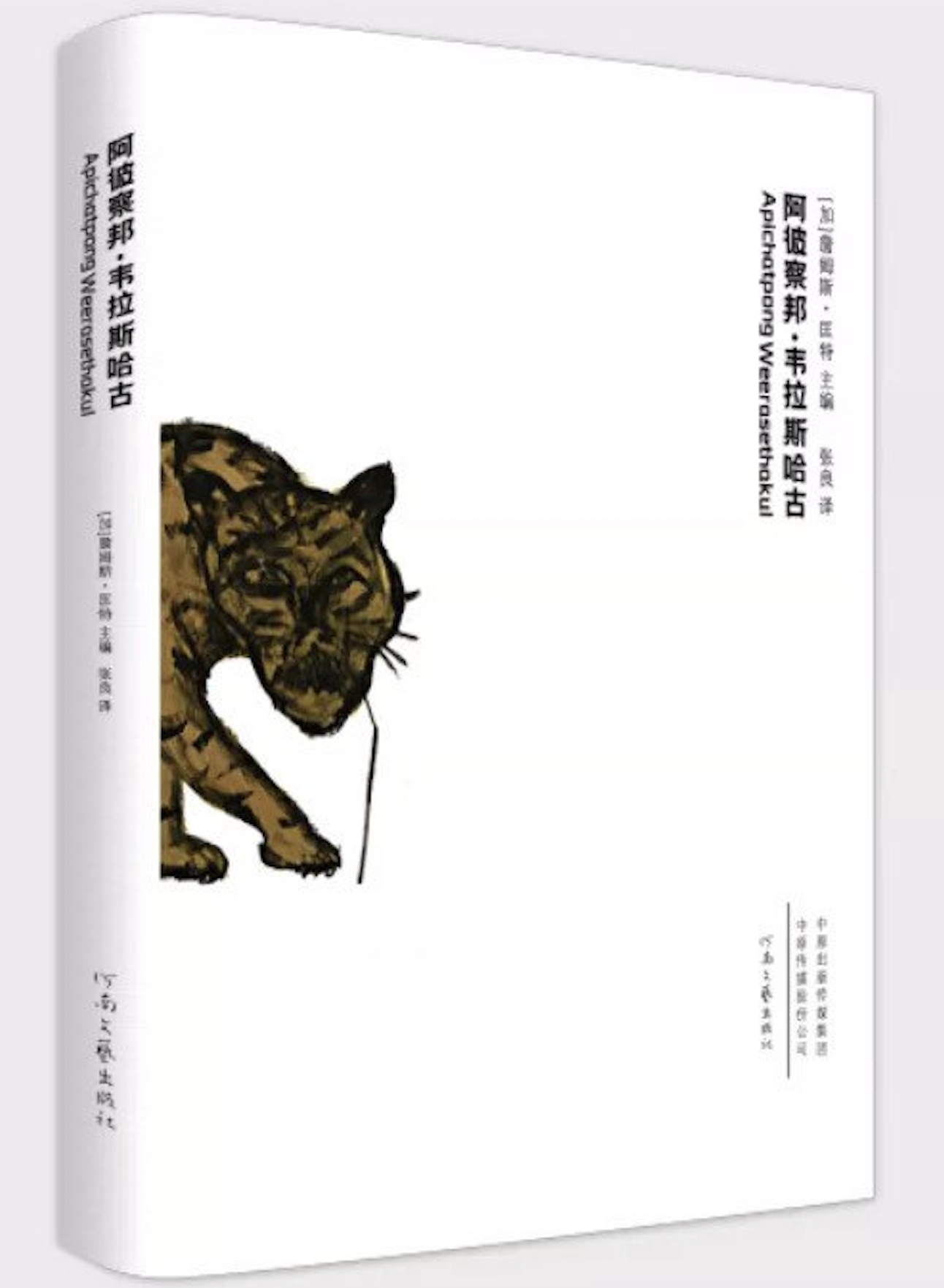
两年前,我在曼谷的泰国国立法政大学为大约100位教授和学生做过一次演讲,演讲结束时,我借着这个机会请听众中听说过阿彼察邦和他令人惊叹的电影《热带疾病》1(2004年)的人举手。令我惊讶的是当时只有15个人举手。当我请真正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举手时,就只有八九个人了。怎么会这样呢?毕竟阿彼察邦曾在2004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审团大奖,而戛纳电影节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他的这次成功也不是一时侥幸,因为两年前他的电影《祝福》2(2002年)就在戛纳获得过另一个重要的奖项。要知道泰格·伍兹甚至都不会说泰语,曼谷的公众仍然急于把他称作“世界一流水平的泰国人”。我想有人可能也会以为泰国人一定会为阿彼察邦这令人赞叹的成就感到非常兴奋和自豪吧!可惜并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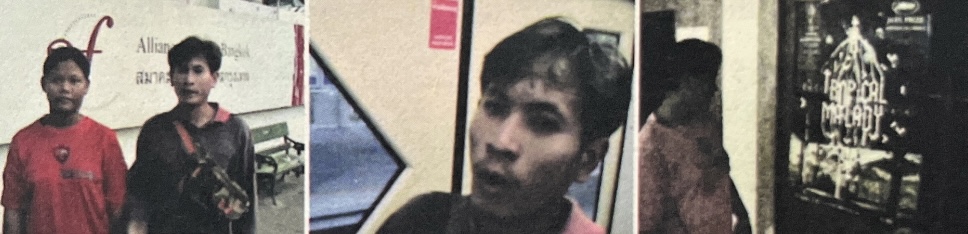
如果有人看了“阿隆科特”3的名为《一起来谈谈“热带疾病”》(2004年)这部聪明、尖刻和有趣的仿纪录片的话,那么上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会初露端倪了。这部仿纪录片反复告诉观众们,《热带疾病》只在曼谷的三家电影院上映,而且每家电影院只上映一周4。为什么呢?接下来是一系列对各类曼谷的小众名流和“意见领袖”们的简短采访,他们都说这部电影“很棒”,“非常有趣”,达到了“高于其他泰国电影的世界级水准”。(貌似他们回应的是戛纳的获奖,而不是电影本身。)但他们却把这部电影描述为“超现实的”和“极为抽象的”(abstrak maak),这表明他们根本不理解这部电影,而且他们都认为在外省的电影院放映这部电影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远远超出了乡下人(khon baan nork)的简单(cheuy)头脑所能理解的程度。
随后,这部仿纪录片对四位年轻的村民(chao baan)(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进行了一段精彩的长时间采访。他们被带到曼谷,在法国联盟举办的一场特别放映会上观看了《热带疾病》。电影结束后,画外的采访者告诉这四个人许多曼谷的知识分子觉得这部电影“难以理解”(yaak)和“神秘”(lyk lap),并询问他们是否有同样的感觉。结果村民们都说这部电影很棒,没有什么特别难以理解或者神秘的,而且他们很希望在家乡的电影院看到这部电影。他们说他们完全可以理解。我们稍后将再讨论他们反应的一些细节。
在转到为什么戛纳和村民们都喜欢这部电影而许多曼谷人却不喜欢这部电影之前,我有必要向大家报告一下我最近与木孔·旺特、梅·英加瓦尼一起进行的一次短暂的业余研究之旅。我们决定花两天时间采访在春武里府、龙仔厝府、沙没颂堪府、叻丕府、素攀府和大城府的录像店工作的人,这些店都距离曼谷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围绕曼谷形成一个大致的半圆。这些店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要开在市中心的租铺,另一类通常开在商场里,它们都以非常低的价格出售正版或者盗版的DVD。我们有什么发现呢?首先,除了在素攀府的一家小店外,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知道《热带疾病》这部电影,而且许多店的货架上都有这部电影的DVD。他们是怎么知道这部电影的呢?不是从报纸或杂志上,而是来自电视上的介绍,还有最有趣的是:来自顾客的需求。当我们问及什么样的顾客对《热带疾病》感兴趣时,最常见的回答是:“哦,各种各样的顾客都有,大多数是家庭顾客。”另一些人则说是“已经工作的年轻人”——也就是20岁到30岁出头的年轻人而不是少年,但也有人说他们有来自十几岁的顾客的需求。大家对这部片子的反应怎么样?回答是“还可以”、“一般”、“需求稳定”。换言之,它不是非常成功,但也不算失败。一位店员告诉我们这部片子的顾客主要是男性,但其他人则否认这部片子的顾客有任何性别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顾客都不是村民(chao baan),而是住在外省小城市的人。
现在,我们可以转向电影本身从而深入理解我们的调查。除了一个神秘的序幕之外(先是一群年轻的士兵在乡下偶然发现了一具尸体,后来我们看到在远处有一个裸体男子的模糊身影正在穿过丛林边缘的高草丛),《热带疾病》的上半部分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英俊的年轻士兵(Keng)是如何追求一个在当地一家制冰工厂工作的长相古怪的年轻人(Tong)的。在影片中,这两个人从未脱掉衣服,也从不亲吻对方,更别说发生性关系了,但影片向我们展示了生活在广大的乡村和小镇环境中的村民之间相互追求的过程。
在《一起来谈谈“热带疾病”》中,扮作曼谷中产阶级的采访者多次询问那四个村民有关这段恋情的问题:“在乡下真的有男人爱上男人的事情吗?”村民们很平静地答道:“哦,是的,这很常见。”他们都认为Tong 和Keng真的爱着对方,其中一位最害羞的男孩甚至说这段恋情很“浪漫”,而那个女孩则笑着说Keng 躺在Tong的腿上的那一幕让她起了鸡皮疙瘩。采访者假装对这一切感到惊讶,问女孩她是否认为Keng可能是一个娘娘腔(kratheuy5)士兵。她咯咯地笑着回答:“是的,士兵很可能是一个娘娘腔。”Tong呢?“嗯···他看起来有点害羞·嗯···很可能他也是。”很明显,这部仿纪录片试图证明两个年轻男人之间的恋情在乡村地区是非常常见的,而对一些曼谷人来说,这种恋情可能看起来却是“赶时髦、仿效西方的”、“可耻的”,甚至是“非泰国的”。[但是在采访者使用Kratheuy这个词之前,村民只使用男人(cha)或人(khon);这些男孩并没有把Keng和Tong描述为娘娘腔]。
然而,细心的观众很快会注意到上半部分的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特点——声音。上半部分完全没有使用背景音乐,取而代之的是日常乡村生活、摩托车、狗吠以及机器工作等声音,而且大多数无关紧要的对话也基本上可以看作“背景”声音,不必认真关注它们的内容。前景则是面孔、表情、肢体语言以及用眼睛、微笑的嘴唇进行的无声交流。Tong的老母亲的表情说明她了解他们的恋情,但她什么也没说,村里其他人也一样什么都没说。如果一个曼谷的观众不注意这些声音上的异常,他很容易就会把上半部分当成很简单的(cheuy)可以忽略的部分,甚至想知道这两个人什么时候才能最终脱下衣服投入彼此的怀抱。
然而,对于这些观众来说,真正的问题还在影片那令人吃惊的下半部分,因为下半部分几乎没有人说话。Keng独自一人进入丛林,寻找一只怪兽(sat pralaat),据说它一直在捕食村民的牛。在下半部分,声音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我们大部分时间听到的都是丛林里的各种声音,以及Keng往丛林里越走越深时发出的声音。而且下半部分主要发生在夜里。当Keng追踪他面前令人迷惑的人和动物留下的脚印或是爪印时,他似乎意识到了它们可能属于同一个生物,而这个生物就是巫虎(seua saming ),但同时也是Tong。最终他被一头野兽袭击,而这头野兽就是观众在序幕中看到的那个奇怪的裸体人。它就是Tong,除了脸上有自己画上去的虎纹,他完全是人的样子,他不说话,只是低吼和咆哮着。在随后的肉搏战中,Tong 是胜利者,他把被打晕的Keng拖到陡峭的山边然后推了下去。他并没有想杀死Keng(更不用说吃掉他了),Keng伤的也一点都不重。我们最后看到的是Tong站在山顶的远远的轮廓,似乎是在确认Keng真的没问题。在影片余下的部分,观众跟随着Keng继续着他的搜寻,体验着各种“神奇”的事件。(一只被吃掉一半的死牛居然完好无损地站起来并消失在丛林中,一只聪明的猴子给Keng各种建议等等。)影片的结尾是 Keng跪在泥泞中,抬头看着他面前一棵树上一动不动蹲着的老虎。我们听到他内心的声音:“怪兽,请你带走吧,带走我的灵魂、我的血、我的肉、我的记忆……我的每一滴血里都流淌着我们的歌,一首幸福的歌……就在那里……你听到了吗?”
怎么理解下半部分呢?当我在马尼拉给一些受过高等教育、中产阶级的菲律宾同性恋放映这部电影时,他们很快就认定这是在日本首创并传播到韩国、中国、印尼、菲律宾等地的“现在非常流行的又一种类型的亚洲恐怖电影”。这与接受“阿隆科特”采访的年轻村民的反应完全不同。其中两个男孩有过丛林生活的亲身经历,他们对电影的评价是:可怕(sayong)、紧张(tyn-ten)和兴奋,有时候甚至头发都竖起来了。他们从没见过巫虎,但确信“它们以前是存在的”。唯一让他们困惑的是最后一幕,他们觉得这一幕被剪短了,似乎没有结束。
一个更有趣的反馈来自我的亲密朋友本·亚伯,他是一个印度尼西亚达雅族人。他是由信仰万物有灵的祖父带大的,他们四十年前住在广阔的、几乎没有人烟的婆罗洲丛林的边缘。当我问他下半部分是否“难以理解”时,他说:“一点也不,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经常在丛林里打猎,有时也在晚上,有时和祖父、朋友们一起,也有时甚至是独自一人。他能立刻辨认出电影声音中所有的动物和鸟类的叫声。“丛林是一个你必须一直注意听各种声音的地方,而你自己要尽可能保持安静。是的,它可能是可怕的,但它就像一个自成一体的奇异而美妙的世界,你会一直想要回到那里去。你知道你在考验自己,同时也在了解自己。”
当我问他关于巫虎的事情时,他证实了尼迪·洛斯里翁斯教授6对我说的他小时候听到的话:“真正的巫虎常常是男人。因为只有男人才有精神力量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的外形,他们可以表现为老虎的样子,但在老虎的外形之内则是人的智慧和灵魂。它们常常会变形以躲避一些危险,这些危险主要来自其他人。还有另一种巫虎是女性,但它是一种幽灵而不是人,它可以变成老虎,也可以变成美女,但它总归是一种邪恶的幽灵。”《热带疾病》的下半部分有个很短的一幕(刚看到时似乎有些令人费解),它表现了Keng的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战友在丛林边缘担任夜间警卫,突然一个美丽的女人出现了,请求他去帮助她生病的母亲,但这个士兵拒绝离开他的岗位,并让她马上回家,因为夜晚的丛林对女人来说太危险了。当她转身时,士兵注意到一条长长的老虎尾巴从她的裙子下面掉了出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里出现的这个女人是邪恶的幽灵变的,也同时表明了Tong 不是幽灵,而是人。
“但无论怎样,”本·亚伯接着说(大意),“你知道如果你像我以前一样在丛林中或者丛林附近长大,城里人的那种与动物世界的距离感就不存在了。你开始理解鸟类和野兽发出的捕猎、交配、逃跑、警告等不同声音的含义。此外,人死后可以从一个世界到达另一个世界,比如人可以通过一只猫头鹰在夜里的叫声认出它是自己最近去世的叔叔。当人们睡觉时,他们的灵魂会离开身体,有时候在梦里带回一些信息。”另外他补充说,他认为在影片的后半部分,Keng是在寻找一些关于自己、Tong 以及其他许多他不明白的事情的答案。
“结尾的美妙之处在于,Keng的爱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愿意放弃‘他的灵魂,他的身体,甚至他的记忆’,换言之,这种人类的观念像是神,与自然世界的其他物种都不同。他的灵魂正在追寻Tong的灵魂。”他最终的总结是,“这是我看过的最精彩的电影。我真不敢相信今天有人能拍一部走进我曾经成长的那个世界的电影,并把它呈现得如此完美。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2005年夏天,我应邀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地点是巴西北部海岸的一个偏远城镇福塔莱萨,它就在广袤、空旷、荒凉的内陆大草原塞尔唐地区(Sertao)旁边,许多巴西传奇故事和电影都起源于这片大草原。我在市立博物馆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那是一个手工缝制的小册子的展览,这些小册子大约都在二十页左右,封面上有粗糙的蚀刻图案。它们主要在公交车站出售,卖给非常贫穷的人,通常写着优美的诗歌,而且一般都没有作者署名。诗歌的主题常常是著名的叛乱、屠杀以及从前的奇事,但这些收藏品中有一部分专门讲述了一些悲伤的女孩和她们的山羊之间,还有牛仔和他们的马、驴之间动人的爱情故事。当我向那些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朋友问起这些故事时,他们的回答很像曼谷人:“好吧,你知道塞尔唐草原深处的牧场里没有女人,所以男人们要么和男人发生性关系,要么和他们的动物发生性关系,你还能指望什么呢?”这似乎难以令人信服,我回应说:“那个可怜的女孩和心爱的山羊一起逃离她那残暴的主人该怎么解释呢?还有那个出于嫉妒而割断马的喉咙的妻子呢?牛仔和他的马相爱了,但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有发生性关系啊?”“嗯,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我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真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如果说(在我看来很可能如此)阿彼察邦不是试图拍一部“关于”泰国村民(chaobaan)的电影,而是试图拍一部从他们的世界“内部”产生的电影,更进一步说就是从那种文化和意识中产生的电影,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阿隆科特”的四个年轻受访者觉得这部电影既清楚又吸引人了,而反过来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今天生活在曼谷空调房间里的许多城里人会觉得这部电影“令人困惑”以及“神秘”了。因为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所处的上层社会已经习以为常了,在他们看来,村民(chao baan)被加入电影中只是为了增添一点附加效果,比如地方色彩或者滑稽感。他们对于在查崔查勒姆·尧克尔殿下的电影《公民》(1977年)中扮演主角的穷小子来自伊善地区7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只是认为如果主角是一个皮肤白皙、完全是曼谷人的漂亮男孩,这部电影就更加优秀了。他们喜欢托尼·贾在《拳霸》(2003年,由普拉希亚·平考执导)中令人惊叹的武功,只是如我听到一些穿着考究的女孩从位于棠林詹区中央商场的电影多功能厅出来时的对话中所说的:“可惜这个英雄不够英俊。”8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他们确实喜欢泰国传奇故事改编的电影,但为了让他们满意,这些电影所使用的必须是那个众所周知的版本,而且观众必须能够与之保持一定的人类学距离。9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非常流行的最新版本的《鬼妻》10(1999年,由朗斯·尼美毕达导演),它按照曼谷的中产阶级电视观众的口味再现了一个原汁原味的恐怖民间故事。对于这个民间故事,每个泰国人都至少粗略地了解它的轮廓。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的丈夫去打仗了,而她在生孩子的时候死去,成了一个渴望复仇的女鬼。在这部电影中,这个女人仍深爱着她的丈夫,她以鬼魂的身份回来并且神奇地重现在他面前,就像她还活着的时候一样。当村民们试图让她被迷惑的丈夫看到真相时,她猛烈地进行着报复。所以说“这是一个爱情故事”,鬼妻根本不是怪兽,而是一个即使死后也不忍离开丈夫的好女人。现在我们可以看出阿彼察邦的巧妙之处:《热带疾病》在某些方面具有传奇性,但它并不来源于人们平常熟悉的任何传奇故事。为了保证这部电影不会“曼谷化”和“庸俗化”,他策略性地引入了男人爱上男人(chai rak chai)的主题,就像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把蛇女(Nang Naak)变成蛇男(Num Naak)的情况!
但我觉得《热带疾病》为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提供了更多的解决思路。这是关于何为“泰国性”(khwampenthai)11的难题。几年前,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和批评家苏吉特·旺提奥的开创性和反传统的著作《中国和老挝的结合》引起了震动,该书认为“泰国性”并没有悠久的历史,而是长久以来中国和老挝文化相互渗透而形成的较新的产物。12
我听说苏吉特对于有些读者给他寄来感谢信十分惊讶,他对中国性(khwampenjek)的正面评价令他们激动、感动。(这种动情的反馈不由让人想起同性恋们看到第一部以迷人的男女同性恋人物作为主角的严肃小说后的反应:“我们终于被真诚而且充满尊重地表现了。”)
中国移民及其后代的历史和文化中确实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而且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许多书都表达了“亮出华裔(jek)身份”的精神,但我们不清楚的是,这些书是否被很多其他身份的人仔细阅读过,迄今为止,我们也还没有看到泰国中小学教科书中有赞美“泰国华人”的内容。
直到19世纪曼谷仍是一个中国移民占大多数人口的城市,甚至在二战前夕,伊善人开始大量涌入之前,曼谷的劳工阶层都主要是由中国和越南移民构成的。今天曼谷成功的中产阶级主要是华裔(lukjin)(即中国人的后裔,或者说华裔泰国人,这是一个比Jek有礼貌的替代词)13。2在很多国家,成功的城市中产阶级在文化上都与乡村地区的人不同,但他们并没有种族差异;但在泰国,由于中产阶级的族裔源自国外,所以这种差异是双重的。
人们可能会这样认为: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泰国华裔(lukjin)中产阶级精力充沛、雄心勃勃,而且在社会上不断攀升,因此他们会倾向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上层阶级和整个国家的文化,就如今天的伦敦上议院挤满了成功的中产阶级,他们热衷于获得某某男爵夫人或者某某男爵的头衔。曼谷也有很多想成为坤英(Khunying)的泰国华裔女性14,这些人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被泰国的“官方民族主义”15所吸引——特别是电视播放的“历史”剧、各种庆典仪式以及“国王之河”这样的宣传机器。16只有他们在扮演“泰国中产阶级”而不是泰国华裔(lukjin)角色的时候,他们才能在脱口秀和电视肥皂剧中看到自己,这当然无法令他们完全满意。他们一点也不喜欢像《冬阴功》(原意为一种受欢迎的泰国辣汤的名字。2006年,由普拉希亚·平考导演;《拳霸》的续集)这样受欢迎的电影,因为像它之前的《公民》一样,这部电影里扮演残忍和贪婪的恶棍的显然是华裔(lukjin)。
我认为,阿彼察邦的电影对今天的泰国华裔(lukjin)中产阶级来说尤其“难以理解”,不仅因为他们这个群体没有出现在电影中,而且因为它呈现着一种有着古老源头的“泰国文化”,这种文化比他们的文化“落后”,在他们的经验中也是陌生的。他们将这种电影视为“为西方人拍摄的”而不予理会,以此作为自己爱国的证明来抵抗它所带来的隐性威胁。因为西方消费主义文化最大的瘾君子们正是曼谷的中产阶级,所以这里面不可避免地含有自欺欺人的成分。这个观点也许可以让我们回想起泰国法政大学,它有时半开玩笑又半自豪地自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潮汕语大学。17假使我在本文中的论点至少有部分是正确的,那也许有助于解释学生和教师们在面对《热带疾病》那令人赞叹的成功时令人惊讶的无知和冷漠。
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在本文上述的很多地方我都强调了“今天的”,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怀疑曼谷中产阶级与乡村文化的高度疏远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事情。在《热带疾病》开场的字幕中,阿彼察邦提到了他对广受欢迎的“丛林小说”的感激和喜爱,这些小说合称为Long Phrai,是泰国大部分原始森林被合法或非法的伐木者大规模砍伐掉之前,即19世纪50年代早期由诺伊·因塔农18创作的。它们被认为是创造性地模仿了包括柯南·道尔的《失落的世界》在内的很多作品。在这些以当代为背景的小说中,巫虎经常被描绘成有点“怪”但却是真实的野兽,而英雄猎人萨克的思维则是相当理性和科学的。诺伊的读者大多是年轻人,可能大多数还是小城镇的男性,他们有着不同的种族和出身阶层,常常听收音机而不是看电视,去嘈杂拥挤的电影院而不是迷失在网络空间,他们都在没有空调的环境里过着知足的生活,还没有陷入平庸的“全球化”消费文化19。这种老式的小城镇社会(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于龙仔厝府和叻丕府这样的地方,但它在曼谷这样的“天使之城”基本上消失了。
曼谷只剩下那些自称非常喜欢《热带疾病》的“意见领袖”,但他们完全不理解这部电影。我之前提到过,这些“意见领袖”对这部电影所获极高声望的奖项的重视是由于他们希望看到这样一件事:即把这些奖项视为“我们的国家”可以制作国际(sakon)水准电影的标志;因此,他们对这部电影的认可意味着他们自己也达到了国际(sakon)水准。问题在于,国际这个词有着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反面的含义。有时这意味着当今的西方人确实欣赏一些泰国电影,但究竟是哪些泰国电影呢?有很多令人担忧的例子,比如《人妖打排球》(2000年,由永裕·松孔敦执导)、《美丽拳王》(2003年,由亚格差·乌干腾执导),还有《拳霸》和一系列恐怖电影,因为它们在海外的成功,似乎意味着外国人会认为“我们的国家”充斥着拳击手、娘娘腔、变性人以及邪恶的鬼魂。有时这还意味着外国人帮助制作和发行了所谓的“优秀泰国电影”。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好莱坞的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在他的朋友查崔查勒姆·尧克尔殿下的“宏大的民族经典”电影《素丽瑶泰》(2003年版)的最终剪辑和宣传中所扮演的角色。唉,可惜这部电影在海外市场是惨败的,即使在泰国,它所获的利润也低于民粹、民族主义、血腥的《烈血暹士》(2000年,由塔尼特·吉特努库导演),而《烈血暹士》这部电影却不是关于皇室而是关于爱国村民(chao baan)的。
《热带疾病》的出现似乎是摆脱这种困境的一个好办法,因为它受到了外国意见领袖、影评家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世界电影迷们的一致赞赏,这些人都可以被称为“我们这类人”。但不幸的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我们这类人”,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在纽约、东京、巴黎、柏林、伦敦和多伦多的资深影迷们基于长期的知识传统,不希望以任何固定、明确的方式去“理解”一部电影,因此形成了一种技术上称为多重读解的文化。他们可以将罗伯特·布列松令人惊叹同时又朴实无华的《扒手》(1959年)视作一部关于现代城市生活异化的电影、天主教对原罪的反思、对被压抑的同性恋的研究或是20世纪40年代法国政治的寓言等等,不排除还有其他的选择。通常情况下,这种智力投入是在电影美学层次上,而且是法国知识分子与他们在日本和加拿大的“同志们”共享的。
但对泰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智力投入就要困难得多,因为他们天然地希望泰国的国际(sakon)电影既是“世界级或全球的”又是泰国的。这意味着这种投入首先是民族主义的,而根据定义这就不可能是国际(sakon)的。既然他们更深层次的关注是政治性的,那么对任何“真正泰国”的东西进行“多重解读”这样不稳定的做法一经开放,就必然会面临一些公开或隐藏的敌意。像戛纳的评委昆汀·塔伦蒂诺这样的外国人可以喜欢《热带疾病》的模棱两可和高度复杂的叙事技巧,同时仍然可以愉快地说:“这个电影太棒了,虽然我没有看懂。”但对于一些曼谷知识分子来说这种立场不被采用,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很难同时说“这是一部很棒的泰国电影”和“我真的没看懂”。毕竟他们是“优秀的泰国人”,他们就该明确地、毫不含糊地看懂这部电影。而阿彼察邦让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至少在泰国本地,他在接受采访时坚持说他的电影完全是泰国的,根植于泰国传统,其中包括泰国流行电影的传统。曼谷的“意见领袖们”即使不是完全忠于“国王之河”式的官方民族主义,也仍然很难理解为什么这种民族主义的花费巨大的产品(比如《素丽瑶泰》)在国际层面上却没人感兴趣。因为那只是一部无聊、过时的电影——只适合人类学专家看看,对非泰国观众毫无意义。毋庸讳言,这些人并不喜欢听到国内的官方爱国主义在世界舞台上是过时迂腐的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有说服力的回答是:他们没有搞清楚旅游业和世界电影之间存在着一些区别。泰国的旅游业已经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功,它让短期度假者们匆忙享受着宏伟的宫殿,壮观的玉佛寺,古老的苏霍泰、帕侬荣和大城府遗址,海滩度假胜地芭提雅、普吉和苏梅岛,还有泰国的食物、泰国的友好以及各式各样的泰国性产业。但这些享受都是肤浅的,只适合身在泰国的度假者们,他们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市场。另一方面,背包客、退休人士、度假的日本商人等在当地的享受与国际影迷的满足感之间也没有任何关系。这种差异会让一些受过教育的曼谷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曼谷成群结队开心地买票参观大皇宫的外国游客,却对在柏林或鹿特丹观看《素丽瑶泰》毫无兴趣。因为那里的观众并不把自己当作游客啊!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曼谷的“意见领袖”们发现自己在“泰国性”的代言人和国际(sakon)文化一员这样的双重身份之下陷入了困境。由于国际(sakon)文化界欣赏阿彼察邦,所以他们也希望欣赏他,但却因为“无法看懂他”而沮丧。摆脱困境的方法就是坚持说《热带疾病》是“难以理解的”和“神秘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它被称作非常“抽象”以及“超现实”的,并因此被认为完全不适合在农村和内陆小城镇发行。
毫无疑问,阿彼察邦很享受这一切。这就是为什么他电影的名字如此多义。在今天的泰国,到底谁是“怪兽”呢?这无疑是个令人尴尬的问题。
附言:其他地方的接受度
自2006年9月军事政变以来,泰国所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仅仅在泰国社会不同阶层和地区之间讨论《热带疾病》接受度的问题已经不够了(假设确实有这种讨论的话)。2007年初,阿彼察邦的最新电影《综合症与一百年》(泰文名为Saeng Sattawat,直译“世纪之光”)在国际上各个电影节的放映都非常成功,但国家审查委员会(一个警察、官僚和一些勉强算是知识分子的人组成的混合体)审查后,坚持必须删除四个简短的场景之后才能在泰国上映。在其中两个场景中,佛教僧人被描绘成审查者无法容忍的样子:第一个场景,我们看到一个年轻的僧人在弹吉他;第二个场景是两个年纪相差很大的僧人正在公园里玩一个充电的玩具飞碟。另外两个场景则发生在医院里20:第一个是一位疲惫的中年女医生,在一天劳累的工作结束后,她拿出藏在假肢中的一瓶酒与几位年轻的同事分享;第二个是一个年轻医生在忘情地亲吻他的女朋友,而镜头短暂地移到了下面,一只手抓着他裤子里的勃起之物。
审查员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电影观众,他们对影片质量和商业成功都不感兴趣。虽然他们通常与曼谷中产阶级一样都看不起边远地区的人,但作为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他们有着官僚机构传统的家长式作风。因而他们觉得有权决定银幕上看到的东西哪些是对“幼稚的”大众好的,尤其当银幕上是泰国电影而不是外国电影的时候。(没有什么比阿彼察邦的电影更可接受的了,他的电影深切地同情乡下人,并且几乎看不到政治的影子。)他们也不需要公开为自己的决定作出解释,但这些决定足以说明那些被要求删除的场景“冒犯”了他们对“泰国”行为规范的保姆式的观念。事实上,泰国报纸上充斥着僧人们性犯罪、金融操纵、吸毒等丑闻,但通常情况下这些僧人的名字都会被曝光,即被看作个人行为,而且这类事情只能通过报纸才能接触到。而阿彼察邦所做的只是以移动影像的方式展示了一些没有署名的僧人(所以可以说是任何僧人),他们正在以一种那些望猎取丑闻的报纸根本不会感兴趣的方式享受生活而已。即使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僧人们也在享受着一些乐趣,但官方的、民族主义的佛教立场仍然认为僧人们必须是甘于奉献的、智慧的、简朴的、永远严肃的人,因此阿彼察邦的轻微的讽刺都会被看作对佛教的亵渎。泰国人是很喜欢饮酒的,如果一些医生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不在医院里喝一两杯,或者不抽出一点时间在私密的角落里亲吻自己的女朋友或男朋友,那才令人奇怪。但国家试图通过树立权威、朴素、智慧和严肃的公众形象来维持泰国医院的威望和公众对泰国医生的信任。21可以这么说,医生就像是世俗僧侣。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虽然不是阿彼察邦第一次遭遇审查制度,但这是他第一次遇到来自国家层面的审查。但阿彼察邦拒绝剪掉任何东西,并撤回了他在自己的国家发行这部影片的申请,这无疑令审查委员会非常吃惊。22这也是泰国电影人第一次没有向审查机构屈服,也没有试图与审查机构讨价还价。
尽管我们无法确定,但在九月政变之前的电影审查委员会也许会有不同的反应,毕竟当年《热带疾病》没有遇到任何审查或者禁令。但可以肯定的是,长期以来他们有着双重标准,像外国电影、特别是好莱坞电影,尽管有着血腥暴力和非常露骨的性行为,却经常可以不受审查地发行,而泰国电影则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管。自政变以来,对媒体的审查变得更加强力、细致和专断。此外,政变的领导人面对他们的敌人,即他信的民粹式的民族主义时认为有必要实施(并加强)传统、官方的民族主义,它们的三个标志是君主、佛教和国家——并由此导致形式主义、委婉隐晦和墨守成规。虽然可能性不太大,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阿彼察邦早先的行为或许与众不同,但至少没有正面直接的冲突,也许从2007年开始,他把自己的遭遇看作言论自由正受到政变者和国家机关压制的很多人的遭遇。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的电影的政治化在加强。虽然《祝福》表面上无关政治,但其男主角是一个贫穷的、来自缅甸的非法移民,两个保护他、爱他的泰国女人警告他必须装作哑巴,这样他就不会因为说话而暴露。这些缅甸劳工逃离了自己国家贫穷和无休止的压迫来到泰国,却经常成为冷酷的泰国雇主、警察、军队、黑帮以及社会敌意的受害者。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这部电影显然是站在缅甸男人和他的泰国朋友这一边的。《热带疾病》似乎也无关政治,但这是第一部严肃、强烈地聚焦男人之间爱情的泰国电影,这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官方禁忌。23
因此,在拒绝了审查机构的要求后,阿彼察邦与同事、朋友,还有他的支持者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家一起,在去年五月份组织了一场针对整个专断的审查制度的严肃抗议,要求至少给泰国(和外国)电影一个理性、清晰、公正的评级系统。
不过,在某些方面,国家审查制度可能还不如另一批不太显眼的人施加的潜在影响大,他们大多与审查机构一样对电影质量漠不关心,但对商业上的成功更感兴趣。这些人就是曼谷的企业家,他们或多或少地控制了新电影的投资,拥有这个国家的电影院和多功能影城,控制着VCD和DVD的制作,特别是发行。他们也都很富有,可以在各种国家机构中建立起强大的关系网。本质上,我们在谈论的是一个有时相互竞争的卡特尔,它们是三个泰国华裔(lukjin)“家族”的商业帝国!因为我们的重点是阿彼察邦和《热带疾病》,所以本文在这方面不会过于深入细节。但简单而言,这里的“大人物”是目空一切的“江老板”,又名江泽泰或者颂萨(SomsakTecharatanaprasert),他控制着沙哈蒙空国际电影公司24,生产本国电影以及进口流行的外国电影。他还间接控制着SF连锁影厅和多功能影城,这些影院有权决定哪些电影能够上映,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好像阿彼察邦早期为他的电影筹集资金时也曾找过江老板,而且某种程度上算是成功了,因为《祝福》的泰国DVD和VCD都是由沙哈蒙空电影公司签约制作和发行的。阿彼察邦声称合同中有一项条款规定任何删减都需要经他同意,但事实上影片在从未征询他意见的情况下仍被删减了。他那时正忙着准备《热带疾病》,虽然很无奈,也只好让那个被删减的版本通过了。而这个电影的原版DVD是在巴黎制作的,并没有在泰国正式发行。影片的最后一幕25都没有机会被国家审查就早已被私人企业果断地剪掉了。不出所料,阿彼察邦和江老板闹翻了。这就是唯一一个在戛纳获得了最高奖(实际上是两次获得了最高奖)的泰国导演却没能加入从曼谷来戛纳的资金雄厚的泰国官方代表团的原因,这可能也是《热带疾病》从未在泰国内陆地区上映,而且只在曼谷的一家电影院上映了三周的原因。
但《热带疾病》的这种命运不能简单地只归咎于沙哈蒙空公司,还应该解释为它与电影卡特尔的另一个成员的串通,那就是Major Cineplex 集团。它由维苏特·普沃莱拉克斯和他的家族所控制,他们拥有泰国最大的连锁影城(可能占据了70%的市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放映和分销帝国。
这个卡特尔的最后一个成员是GTH,这是一家电影制作公司,它由泰娱乐公司和HubHoHi制片公司合并后(受行业资金问题的影响)加入另一个综合娱乐帝国亚洲格莱美传播股份有限公司26而组成的,老板是被称为“AhKoo”的黄民辉27。不同于卡特尔的其他成员,“AhKoo”会听取一些好的建议,支持一些有才华的年轻导演使用先进的技术拍摄电影,但他们制作的主要是创新的主流电影(例如2006年的《鬼宿舍》,还有《美丽拳王》)。这些电影有很多都不错,也很受欢迎,但它们与阿彼察邦的作品还是完全不同的。有趣的是,“AhKoo”在最后关头为《热带疾病》提供了25%的资金,使它可以赶在戛纳电影节交片前完成。28但是GTH不具有沙哈蒙空和Major公司的发行能力,因此似乎也就没有充当阿彼察邦电影的审查角色。
总之,这个卡特尔的问题可能比国家审查委员会更大,因为它的运作不受公众关注,而且根植于巨大的、根深蒂固的经济利益。阿彼察邦的天赋和声誉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绕过卡特尔,依靠海外的(主要是西欧)资金来支持他的电影。但这些支持只能帮助他拍电影,而不能把电影发行给他的同胞。
- 《热带疾病》的泰语片名的字面意思是“怪兽”,指的是民间传说中的可以变形的巫虎。 ↩︎
- 《祝福》的泰语片名的字面意思是“完整的幸福”。 ↩︎
- 阿隆科特是指阿隆科特·迈庄,他以“卡拉帕普吕克”(Kanlaphraphruek)的笔名撰写电影评论。他在他的电影评论集《四位顶级东亚导演》第123-162页发表了一篇非常优秀的对阿彼察邦电影的探索性的调查。他还制作过一些短片在2005年第四届曼谷实验电影节上放映。 ↩︎
- 阿彼察邦写信给我说,它实际上只在丽都(Lido)这一家电影院上映,但放映了三个星期。 ↩︎
- Kratheuy是一个古老的高棉语单词,被泰语采用,意思是喜欢穿女装的娘娘腔男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泰国社会中,即使通常被污名化,Kratheuy人也是一个公认的群体。“同性恋”这个词和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才进入泰国的,请注意,采访者故意提出一个矛盾的问题:一个有男子气概的士兵真的是个娘娘腔吗?想看看村民们会有什么反应。 ↩︎
- 尼迪是公认的泰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专栏作家、讽刺作家和正直的社会活动家。 ↩︎
- 伊善(Isan)位于泰国东北部,是该国最贫穷的地区。人们的主要语言是一种方言,相比作为官方语言的泰语,这种方言更接近老挝语。伊善以流行的民间音乐而闻名。伊善人通常被曼谷人视为皮肤黝黑、粗野、头脑简单的人。 ↩︎
- 托尼·贾的首次亮相在泰国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并在国际市场上大受欢迎。托尼来自伊善,皮肤非常黑。其实他长得很英俊,但那些女孩对男性美的标准主要集中在肤色上。也许我应该补充一点,棠林詹区是湄南河西岸(贫民区)吞武里的一部分,正对着“曼谷”。那里仍然有很多迷人的花园、果园,还有运河,依然保留了某种乡村氛围,很少有外国人住在那里。但它正在被高档化,其中央购物中心对西岸的向上流动的中产阶级来说很有吸引力。不远处则是下层阶级经常光顾的土气的Pata商场,如果你在那里看电影,你会听到观众用伊善方言大声评论和欢呼英雄。
↩︎ - 译者注:所谓“人类学距离”是指这些观众不习惯电影中的人物、事件与生活中的一样,而是希望看到生活中看不到的那种戏剧性事件以及高大英俊的英雄人物。 ↩︎
- 译者注:Nang Nak,这部电影英文译为“蛇女”(Snake Girl),中文一般译 为“鬼妻”。 ↩︎
- 译者注:khwampenthai,或者英文Thainess,即泰国性,是一个即便在泰国文化界都仍有争议的概念,可以简单理解为泰国人之所以成为泰国人的民族和文化特征。 ↩︎
- Jek Mixed with Lao 这个书名是具有挑衅性的。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讲老挝语的伊善人经常被曼谷人看不起,他们也把老挝看作泰国的“小弟”。Jek是一个贬低中国人的词,类似于 Chink。 ↩︎
- 包括皇室在内的上层阶级也有部分中国血统,但这个观点在公众领域并没有被广泛认可。
↩︎ - 1932年泰国政变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后,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所有传统上由国王授予男性官员的头衔都被废除了。奇怪的是,女性的头衔却被保留了下来:据说这种反常现象是少数政变头目的妻子施压的结果。“坤英”( Khunying)是泰国国王授予已婚妇女的头衔,一般有两类情况:第一类是做出杰出成就的人道主义或社会工作的女性;第二类是高阶层的政府官员的妻子。 ↩︎
- “官方民族主义”源于国家而非民众运动,它是在19世纪下半叶由担心民众运动的王朝统治者们在欧洲创立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探讨请参阅我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起源与散布》(1991年版,第6章)。 ↩︎
- 所谓宣传机器,即在曼谷湄南河流经的地方宣传统治者的宫殿、寺庙和纪念物。最初的目的是促进旅游业,比如son et lumiere 表演、豪华的河上游轮等等,但最近它表现出的政治性几乎与其商业性一样明显。
↩︎ - 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移民绝大多数都是讲潮州话的。事实上,泰国法政大学的社会背景与曼谷其他著名大学并无明显区别,但它的这种乐观的自嘲却是独一无二的。 ↩︎
- 诺伊·因塔农(Noi Inthanon)是多产作家和记者马莱·乔菲尼特(MalaiChuphinit,1906-1963)的笔名。这些小说有现实生活的元素,因为Malai自己就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而且,就像主人公和他信任的克伦族向导之间的关系一样,他把带领他进入北碧府丛林中心的克伦人看作最亲密的朋友。 ↩︎
- 事实上,这些丛林小说在电视时代之前已经通过广播连续播出,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
- 这部电影被认为是阿彼察邦对父母的间接致敬。他们都是医生,在伊善首府孔敬的一家医院工作,阿彼察邦也在那里长大。我在2007年5月的一次公开会议上看到了这些被禁的镜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让电影导演和电影爱好者团结起来,反对专断的审查制度。 ↩︎
- 阿彼察邦告诉我,审查者们邀请了泰国医学委员会和佛教僧侣委员会参加了特别的非公开的放映。这些组织由年长的保守主义者把持着,毫无代表性。阿彼察邦狡黠地提出了疑问:这些佛教僧侣委员会的代表是否曾经看过那些当地流行的含有僧侣杀人狂的恐怖电影? ↩︎
- 一位被怀疑是“江老板”心腹的泰国法政大学的教师在一次采访中不留神说漏了嘴,他的言论表明他很看不惯阿彼察邦,认为阿彼察邦“太自以为是了”,“以为自己是个国际巨星”,“亵渎宗教信仰”,“专盯着同性恋”。 ↩︎
- 这是一个面向公众报道什么的问题。众所周知,二战后泰国至少有两位总理更喜欢同性而不是异性,媒体上从未出现过他们与情人在一起的照片,也没有直接提及过他们的性取向。 ↩︎
- 译者注:Sahamongkol,沙哈蒙空国际电影公司,是泰国最大的电影制作和发行公司之一,中国有时也称为佛像电影公司。 ↩︎
- 缅甸男子和两个女人一度逃到丛林中,在那里他们愉快地在小溪中沐浴、聊天、小憩。他精疲力尽地睡着了,那个年轻的女人(即他的情人)看着他,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微笑,她没有吵醒他,把他的阴茎从内裤里掏出来,爱抚着。
↩︎ - 译者注:GMMGrammy,一般译为“亚洲格莱美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
- 译者注:泰文名 Paiboon Damrongchaitham,中文名为黄民辉。 ↩︎
- 如通常情况下的三家大型企业合并那样,GMM、泰娱乐和Hub Ho Hin的领导人在分享新的执行董事会的席位,并将他们的一些员工带进了新集团的结构中。由于集团反对Ah Koo的冒险行为,他就创建了一个自己控制的公司Tifa来绕过集团的控制。但不幸的是,Tifa最近被关闭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