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认为,电影是不朽的;在达米安·查泽尔(Damien Chazelle)最新的电影《巴比伦》中,一位好莱坞(Tinseltown)1的八卦专栏作家大谈定格在赛璐珞(胶片)上的演员得以在后世永生,她这个观点被大量的电影理论学术著作以更高的思想理论反复重申。广告语将珍贵的记忆重塑为“柯达时刻”,以回应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愿望:把稍纵即逝的时间单位冻结为我们可以在闲暇时反复重温的物理量。这种思路可以理解,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点击观看100年前的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录像。但伊娜斯·多哈里雅Inés Toharia2想让大家知道,这在根本上也是错误的。
她在西班牙的家中接受《卫报》采访时说道:“我们的社会走得太快了,以至于我们时常意识不到什么被我们甩在了身后……我们应该停下来思考如何保存我们的数字资料,因为它们不会永远存在。而今天的很多视频甚至并没有打算被保存,比方说监控录像,还有YouTube上的很多东西。我们生产的东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我们没有照顾好它们。一个朋友给我看了他们小孩迈出第一步的视频,我想:‘哦,这视频存不了多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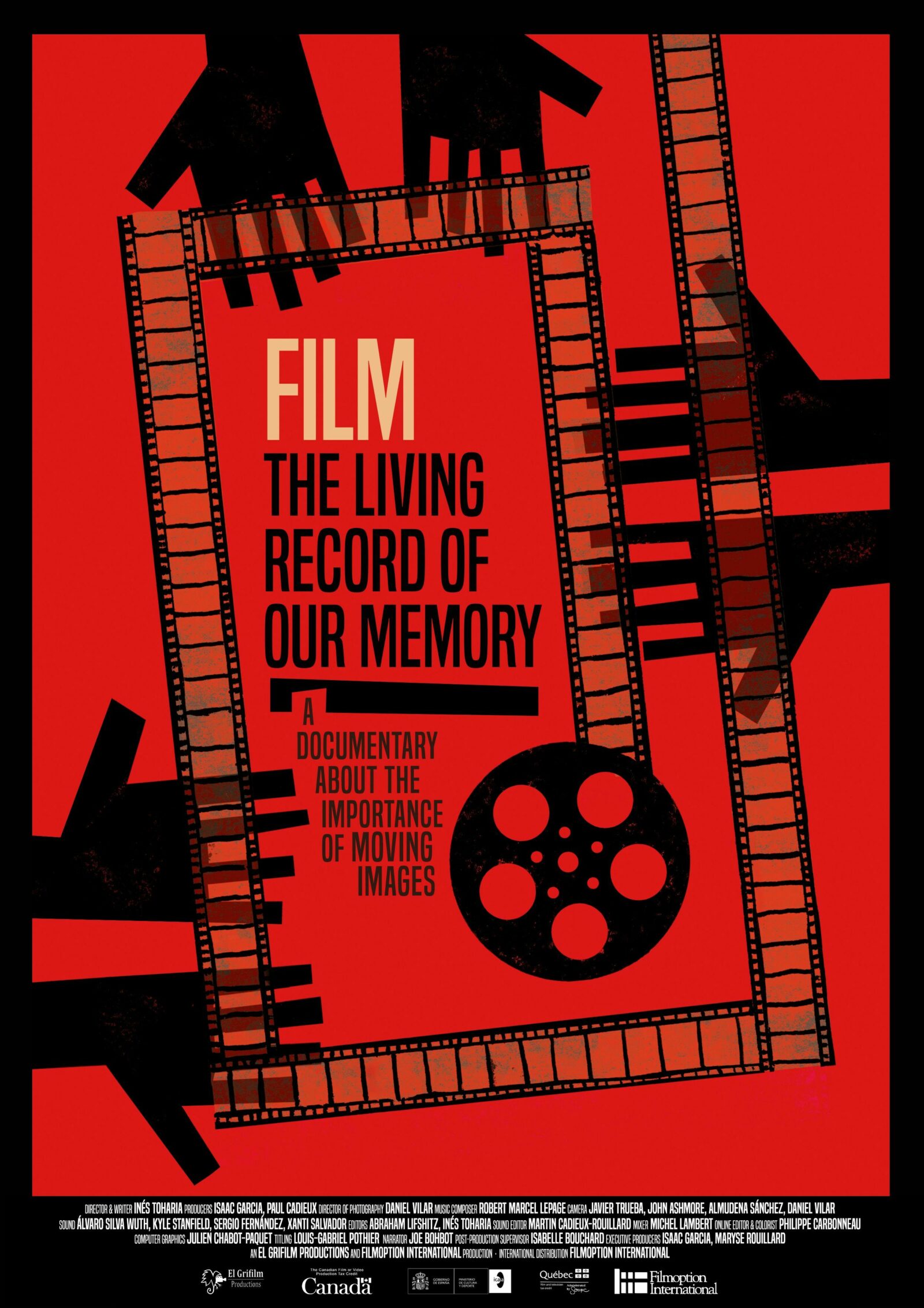
她的新纪录片《记录记忆的胶片》(Film, the Living Record of Our Memory, 2021)探讨了保护动态影像保护这一紧迫话题,从高密度的动态图像历史到对其未来的担忧。电影胶片生生死死,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都会遭到损坏。为了持续获取不断扩增的海量内容——不仅是宝贵的艺术遗产,而且是世界现在和过去的模样——需要由充满激情的专家和电影爱好者组成的全球网络艰苦卓绝地持续修复。多哈里雅的这部有教育意义的视频论文给了这些无名英雄们应有的待遇,明确了他们任务的高风险性,并祝贺每次他们将另一部影片从消失边缘拯救出来时的小奇迹。
“虽然每个人都知道电影文化,知道什么是电影,但我们并不真正了解电影史背后的努力,”多哈里雅说道,“现在看电影很容易——有了云,只要你想看,它们就在那里。但这里面有很多劳动。我们能够享受观看一部电影,往往是得益于某一两个人背后的付出。这一点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这工作收入不高,但他们还是做了,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工作的价值,如果他们不做,没有人会做。”
她从一堂节奏紧凑的电影制作技术速成课开始:我们所知道的电影诞生于一种被称为“胶片”的薄薄的柔性塑料带上,尽管今天许多片子是由带有数据库存储的数码相机拍摄的,但好莱坞大制片厂仍然使用胶片技术来存储每部作品的拷贝。许多品种的胶片能提供最生动丰富和精确的色彩保真度,然而它远不是一个完美的系统。即使有最先进的设施能够将档案的温度控制在零点几度,岁月也会使其容易变形、凝固、硬化和变色。
在探讨这个话题时,多哈里雅必须在外行和内行之间穿针引线。她说:“这个话题很庞大,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担心人们觉得我们的方法过于小众和专业。”我意识到,修复工作必须是真正开放的……有一些关于技术的故事我很喜欢,例如特艺七彩(Technicolor)3——工艺如何不同,为什么它的价值无可估量,为什么它的褪色方式与其他胶片不同。有很多事情我很想深入了解,但我们会因此失去大部分的观众。我想这片可以做一个地基,如果你喜欢这个,你会发现还有很多东西需要研究和学习。我们希望它是有吸引力的,并向每个人展示它们与这个世界的联系。”
修复工作影响着我们所有人,即使是有些人认为自己的观影习惯可能与突尼斯默片开拓者阿尔伯特·萨马·奇克雷(Albert Samama Chikly)5的作品毫无关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让那些在默默无闻中消失的大师们得到应有的认可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每部电影,无论多么普遍,都需要关注和照顾。这种无形的辛劳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现代艺术博物馆对《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1968)的精心修饰(这要求平衡好清理其外观的同时保住影片的原汁原味)到马丁·斯科塞斯的非营利性电影基金会所倡导的流媒体扩展。4“电影里什么都有!”多哈里雅说,“任何你想了解的东西:科学、传统、时尚、发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故事、心理学、社会学。我们通过视觉来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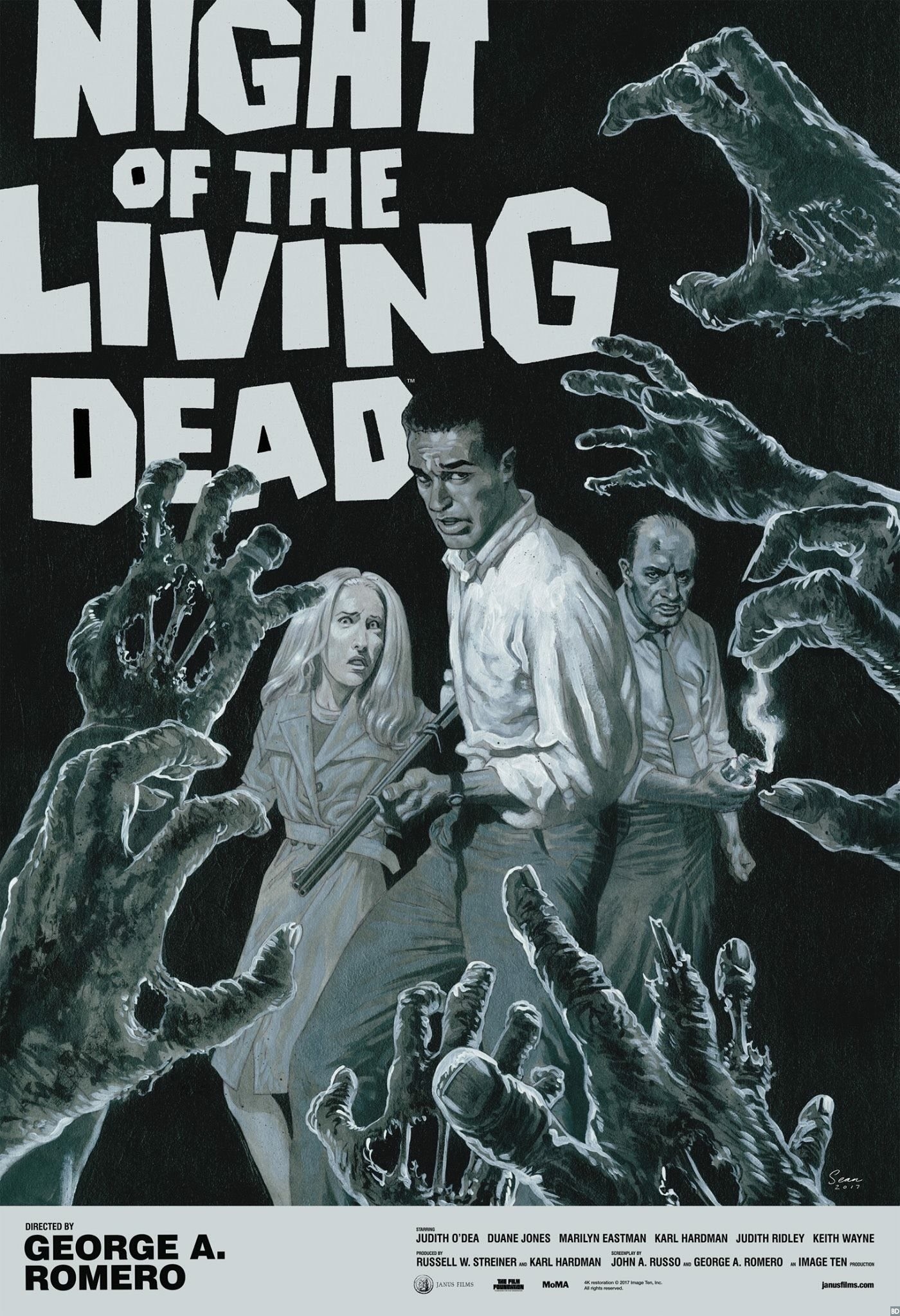

这段话所言不假,并日益真实,因为我们口袋里的相机从十亿个角度拼凑出了我们的现代性。数字存储技术还没有完全解决所有这些原始信息能放在哪里的问题,它的成本令人望而却步,并且需要不断地将数据从硬盘中迁移出来,而硬盘的过期速度甚至比胶片还快。多哈里雅说:“我们已经选择了数字化,没有退路了。”但她在我们目前的计算化范式中看到了新的前沿领域。她影片的最后几分钟谈到了下一代技术的发展,包括一个玻璃硬币大小的硬件,包含了虚拟内存和人工合成DNA,能够将视频压缩进一枚“药片”。
她说道:“数字化很奇妙,在保存方面,特别是在修复项目中,你可以在电脑上做一些漂亮活,而这些事情在光化学无法做到。数字化的进步使更多的电影可以更快捷地存取,但它远非完美和长久,只是保存所面临的问题不同而已。”

随着对热心于此工作的人不断呼吁,这背后付出的汗水和泪水都是为了一桩有价值的事业。在她关于人性的蒙太奇中,多哈里雅剪进了塞内加尔的经典作品《土狼之旅》(Touki Bouki,1973)、印度尼西亚的《海龟妈妈》(Vérité curio Mother Dao,1995)6,以及捕捉到因纽特部落文化的民族志默片。这些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档案文件,是对政治和社会现实的证明,以对抗那些代理人的恶意篡改。尽管我们可能认为这种专为电影的一趟旅程是种奢侈,但这种媒介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作用,那就是将各种重叠的真相拼凑在一起,我们能够从中窥见我们的理念。电影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亮的镜子,我们有责任让它不致破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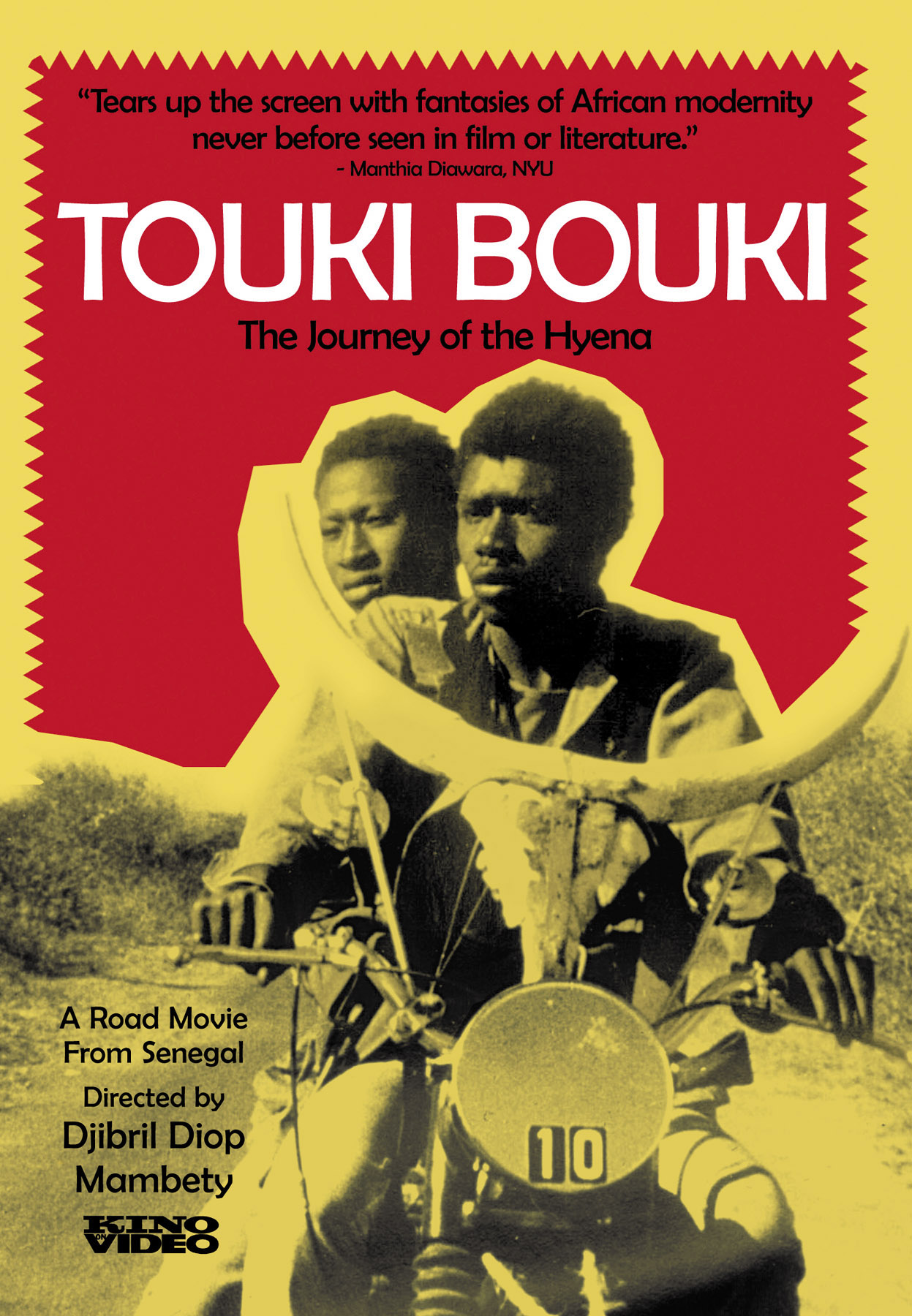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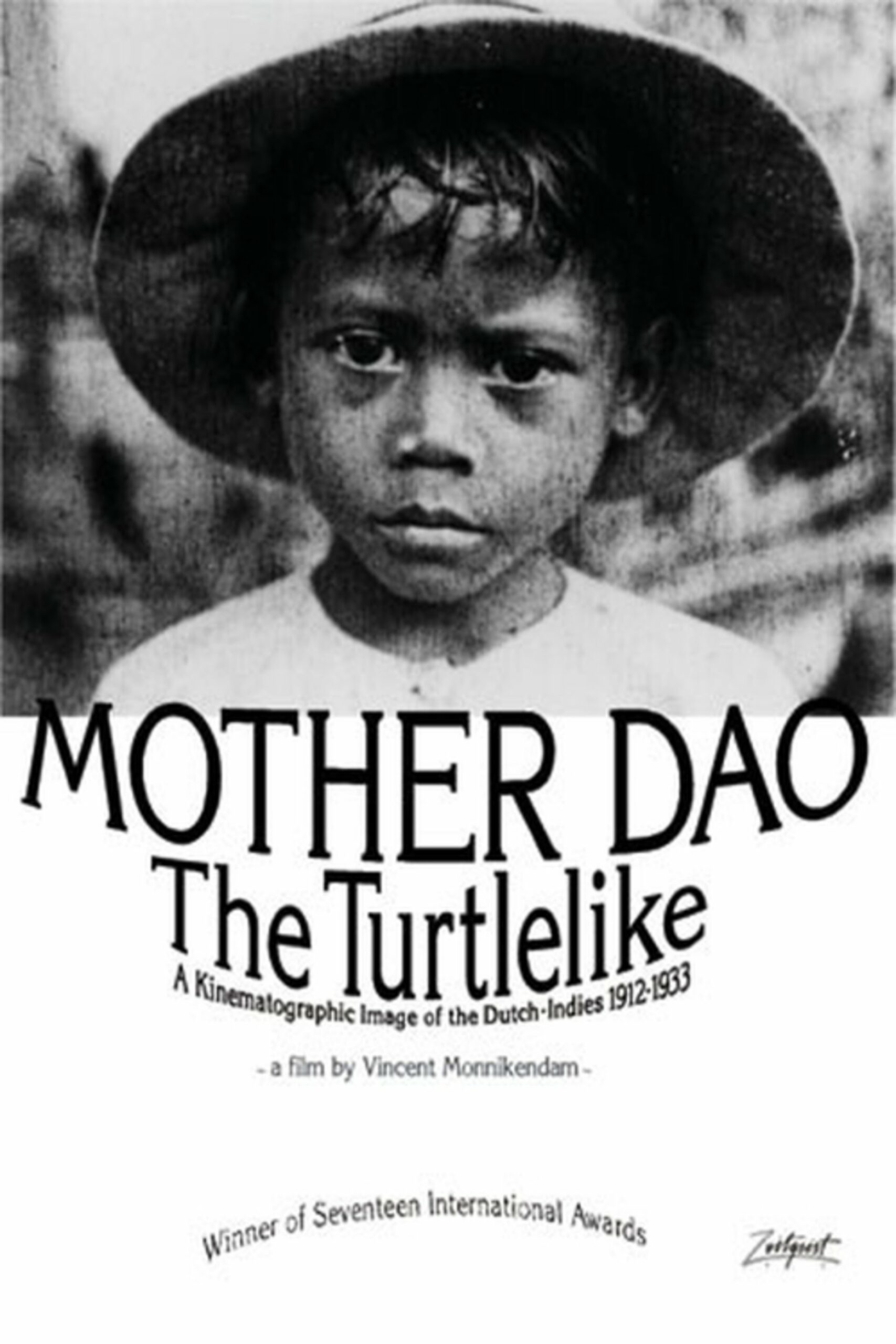
多哈里雅说:“我们必须保留这些,因为我们未曾从历史中得到教训,我们在发展,但是是以商业的方式,仅仅为了利润。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正因不作为而被破坏,我们视若无睹。但是,我们还可以改正。”
注释
- 在这里好莱坞不直接叫Hollywood,而是另一个外号Tinseltown,又指这里是花花世界,名利场;
- 在完成文学和电影的学习后,伊娜斯获得了在英国进行电影制作培训的资助,后来在美国利用富布赖特奖学金专攻电影保护。她导演的纪录片和短片在国内和国际上播出,并获得了不同的奖项。她曾在不同的电影档案馆和文化保护项目中工作(美国、墨西哥、联合国、西班牙),并在撒哈拉难民营合作举办了第一届FiSahara(西撒哈拉国际电影节)。她曾策划过展览和放映,担任过摄影师,报道过主要的国际电影节,并从事电影史的教学和写作。
- 特藝七彩(英文:Technicolor)又稱特藝彩色,是一種採用於拍攝彩色電影的技術,約在1920年代發明,最初應用在美國荷里活的電影製作。特藝七彩技術主要利用彩色濾鏡、分光鏡、三稜鏡,以及三卷黑白底片,同時紀錄三原色光,菲林再進行沖印、染色及黏合過程後,就可以利用普通電影放映機播放彩色電影。早期的特藝七彩由於技術所限,只能紀錄紅綠兩色,並需要以特製器材播放,在當時的商業電影市場中競爭力不強。特藝七彩以呈現超現實色彩及有着飽和的色彩層次而聞名,初時多被用在拍攝對於色彩要求較高的舞蹈音樂及卡通類型影片。很多著名電影使用特藝七彩拍攝,例如:《亂世佳人》、《綠野仙蹤》及《白雪公主》等。
- 世界电影计划(英语:World Cinema Project,简称WCP)是一个致力于保护和修复被忽视的世界电影的非营利组织。马丁·斯科塞斯于 2007 年成立了世界电影基金会(World Cinema Foundation), [1]灵感来自美国电影基金会——一个由马丁·斯科塞斯、乔治·卢卡斯、斯坦利·库布里克、史蒂文·史匹堡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于 1990 年共同创立的类似的企业。世界电影基金会由「电影人委员会」提供顾问支持,该委员会成员包括马丁·斯科塞斯、法提·阿金、苏莱曼·西塞、吉尔莫·德尔·托罗、斯蒂芬·弗里尔斯、亚历杭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王家卫、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迪帕·梅塔、埃曼诺·奥尔米、哈乌·佩克、克利斯提·普优、沃尔特·塞勒斯、阿博德哈蒙·西塞科、伊利亚·苏雷曼、贝特朗·塔维涅、维姆·文德斯和田壮壮。 [2]
- Albert Samama Chikly (24 January 1872 – December 28, 1934),突尼斯导演和摄影师。被认为是“世界电影”(World Cinema)的先驱。
- 在九十分钟的时间里,这部影片旨在展示荷兰是如何将其殖民地作为一项殖民事业来管理的,以及当时的关系是怎样的。在《海龟妈妈》中,纪录片惯常的旁白评论被数字编曲的印尼语诗与歌取代。观众看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殖民机器是如何植入一个与西欧如此不同的世界。
